








李亦園(1931年8月20日-2017年4月18日)[2],出生於福建省晉江縣,人類學家。他在1984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並在同年參與籌創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擔任該院首任院長至1990年。[3]將台灣早期人類學偏向歷史學的治學取向,拓展到社會科學。李亦園將之稱為「社會科學轉向」+行為科學的三大重點學科即是: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而如何將這三門學科,進行科際整合
李亦園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2Hmn6Ax
生平
1931年8月20日,李亦園出生於福建省晉江縣。
1948年,李亦園考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後來又轉入該校人類學系,[4]並在1953年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
1955年至1998年之間,他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歷任助理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等職位,並於1968年至1977年間擔任該所副所長、所長,又曾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評議員、諮詢總會常務委員等院內職務。
1958年,他前往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就讀,師承人類學者John Pelzel、Cora Du Bois等。[5]1960年,他在該校獲頒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學位。
1960至80年代,他經常在報紙雜誌上以理性、淺白的字詞,藉著不同文化的對比評析社會文化現象,以期藉此提昇促進大眾對於相關議題之討論認知。[6][7][8]
1968年至1983年,他在國立臺灣大學擔任合聘副教授、教授,後又被該校聘任為講座教授;其間,他教導出如莊英章、徐正光、黃應貴、黃樹民、陳中民[9]、吳燕和、許木柱、餘光弘、臧振華、胡台麗、陳祥水等知名人文社會學科學者。[10][11]
1984年,他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當時,有報紙以標題「冷門學科出狀元」報導此一新聞。同年(1984年),他參與籌創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並自是年出任該院院長直至1990年。[5]
1989年,他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成立後擔任第一屆執行長直至2001年,並在2001年至2010年間擔任該會董事長;其間,他透過經費補助與獎勵長期致力於推動國際漢學研究。
2017年4月18日,他因急性肺炎病逝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2]
學術研究
研究領域
文化理論、家族組織、比較宗教、儀式象徵、神話傳說等。
研究對象
臺灣南島民族、海外華人及臺灣漢人社會文化。
著作
專書
《文化的圖像》、《人類的視野》及《田野圖像》等。
論文
榮譽
中央研究院最優服務獎(1968年)
總統府保舉最優人員(1968年)
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84年)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1984年、1987年)
海德堡大學學術獎章(1994年)
查理斯大學貢獻獎章(1995年)
行政院文化獎(1999年)[7]
中華民國二等景星勳章(2000年)
巴黎梭邦大學榮譽博士(2001年)
格里菲斯大學榮譽博士(2001年)
國立清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2004年)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2005年)
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文學博士(2008年)[5]
李亦園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2Hmn6Ax
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
人類學家李亦園先生從民國四十一年迄今,一直未中斷對台灣土著民族的研究興趣。其前期的研究著重於民族誌的論著,包括對器物與衣飾標本等有形文化的整理,以及對各族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等無形文化的翔實記錄與完整的分析;後期的研究方向,則以山地社會文化的變遷及其適應問題為主,並且在研究和實際問題互相配合的觀點上,予以進一步的探討。
1972年,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出版了第一本科際合作的研究成果:《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的討論》。出版不到一年,即因其中隱含的批判精神而遭查禁,然禁不勝禁,坊間翻版流竄,港、台皆有,絲毫不影響它的流通性和影響力。2009年,該書被日本出版界選為「東亞百冊經典」。而推動《中國人的性格》出版,引領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科際綜合研究」的主要舵手,便是李亦園先生。1984年李亦園先生榮獲台灣最高的學術桂冠: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亦園,福建泉州人,1931年出生,父母都是書香世家。由於泉州的僑鄉文化有遠渡重洋的傳統,再加上母親的大力支持,1948年,才剛高中畢業的李亦園搭船來台灣報考大學,並順利進入台大就讀。1949年泉州變色,台灣也因此成了李亦園落地生根的第二故鄉。
李先生原先就讀台大歷史系,大二時,學術歷程出現了第一個轉機:李濟之先生的「考古人類學導論」,啟發他對人類學的興趣,大三時毅然降轉考古人類學系(當時的考古人類學系才成立一年,只有大二的課,沒有大三的班,李先生只能降轉。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於1982年更名為人類學系),因緣際會成了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第一屆畢業生,也是台灣本土培育出來的第一代人類學學者。
李亦園另一個啟蒙恩師是凌純聲。凌純聲在1930年代初所執行的赫哲族調查,向來被認為是「中國民族學的第一次科學民族田野調查」。李亦園的第一個民族學田野,就是大四時跟著凌純聲、衛惠林前往花蓮阿美族學習田野工作。1955年中研院成立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凌純聲銜命擔任籌備處主任,而李亦園便是在凌純聲老師的號召下,來到民族所服務。
當時台灣的經濟甚是困窘,中研院的薪資也甚微薄,為了解困,李亦園在菲律賓教書的父親,便幫他在僑居地安排了一個教書工作。1958年,正當李先生要啟程赴菲之際,收到了哈佛燕京學社寄來的入學通知,學術生命因之大轉彎:李亦園決定赴美深造。
在哈佛大學師承人類學者Clyde M. Kluckhohn,是李亦園學術生命又一個轉折點。Kluckhohn是哈佛大學提倡科際整合最力的學者之一,他和著名的社會學家Talcott Parsons、心理學家Gordon Allport、心理分析學家Henry Murray等,共同策劃了代表科際整合取向的「社會關係學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在哈佛期間,「文化與人格」學派開創者之一的Cora DuBois、專研原始宗教的Evon Vogt、日本專家John Pelzel等人的專業教誨,也深深影響到李亦園日後的治學取向。
李亦園堪稱是位「即學即用」的知識份子。1960年代前後的台灣人類學研究,主要有兩大取徑。一是所謂的歷史學派,就是著重在民族文化史的回溯與重建,而田野考察只是佐證史料的從屬工具;二是傳播學派,亦即透過物質文化材料的蒐集與分析,來理解文化史及文化傳播。李亦園自美返台後,便開始思索如何走出台灣早期「描述性」民族誌的窠臼,並透過吸納人類學的理論範式於民族誌的書寫中,以期與國際人類學者對話。除此之外,他也從人類學的學科本質出發,重新思考台灣人類學者的學術使命和研究對象,以期跳脫故步自封,「只守住一地一族」的研究格局。李先生的研究議題也因此從以往所謂「即將消失的高山族文化調查」,擴展到文化的「當代變遷」和「比較視野」;就研究的區域而言,則由當時稱之為「高山族」的原住民文化,拓展到「海外研究」和「台灣漢人社會」。
李亦園1962年所出版的〈台灣土著族的兩種宗教結構系統〉,即是根據他對泰雅族和阿美族的田野調查,提出的綜合性分析,也是台灣第一篇以「比較宗教」的觀點所寫的論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1962)一書,則是台灣人類學著作中,首次使用了「文化變遷」的概念。他所主編的《南澳的泰雅人》(李亦園主編 1963、1964),除了納入泰雅當代的社會情境外,也是臺灣戰後首度以特定理論為基礎(即「文化與人格」學派)所寫成的高山族民族誌。李亦園刊登在《東方雜誌》中有關他的東南亞研究,更是「老文體,新書寫」。當時從事海外研究的學者相當少,很多人不免好奇地探問東南亞研究的種種,李亦園(1967)便仿效宋朝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寫就了〈我怎樣做華僑社會的實地研究〉。他於196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專著,該書以《文化與行為》(1966)為名,便是借用Kluckhohn的著述Culture and Behavior: Collected Essays(1962)為書名,以此感念甫去世的恩師Clyde Kluckhohn,同時也藉此表達他對行為科學的嚮往。對李亦園而言,行為科學的三大重點學科即是: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而如何將這三門學科,進行科際整合,則是他自哈佛留學返台後,一直思索的課題。
在哈佛留學期間所播下的「跨學科思維」的種子,要到1968年,李亦園以38歲青年才俊之姿接下中研院代理總幹事一職,才得以發芽成長。「總幹事」一職使得李亦園得以從「跨院所」的高度,進一步瞭解各所不同學科的學術特色。1970年他接任中研院民族所所長(19701976)後,便以其行政力,將他「跨學科」的視野落實在制度和人才的延攬上。就制度而言,就是在民族所設立「文化研究組」、「行為研究組」及「區域研究組」;在人才的延攬上,則同時進用人類學者、心理學者與社會學者。一言以蔽之,就是將台灣早期人類學偏向歷史學的治學取向,拓展到社會科學。李亦園將之稱為「社會科學轉向」,而這一學術格局的試金石,便是由李亦園和心理學家楊國樞先生所主編的《中國人的性格》。
《中國人的性格》是根據1970年至1972年分兩階段所舉行的講演會論文結集而成。這一系列講演會召集了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哲學、史學等不同學門的學者與會。而當初籌辦的構想,誠如李亦園在該書的〈序言〉所述,希望「促進社會科學科際綜合研究或科際合作的趨勢」;同時,也想藉一個和諧、愉快而又免去「礙於情面」的學術討論會,「促成一種虛心接受客觀批評與建議的風氣」。講演會以「中國人的性格」或「民族性」為題,多少也反映了「古之學者為己」的治學風範。蓋「民族性」這一議題(如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和《菊花與劍》)在19301950年代二次大戰前後,雖說是重點學術,但到了1970年也已到了強弩之末,而李亦園仍以「中國人的性格」為題,實有它對應當時威權政治的時代意涵;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知識份子自清末以來,面對列強侵擾,期能在文化反思中,找到民族定位。用李亦園自己的話說,就是「對自己能多所瞭解,才能在接觸別人的情境下認清自己,而不致於迷失方向」。
從當今的學術發展脈流觀之,《中國人的性格》建立了堪稱「開風氣之先」的四大典範。
典範一,首開台灣社會科學科際綜合研究的新趨勢。
典範二,揭櫫虛心接受客觀批評的學者器識。
典範三,體現知識乃超然於一切政治力與意識形態之上的獨立性。
典範四,彰顯學術研究既在瞭解他者,更在反求諸己、觀照自身。
1972年出版的《中國人的性格》,雖說企圖伸張學術的獨立性,但在威權至上的1970年代,講求批判的學術自主還是受到壓抑,該書即因「批判中華文化」,和當局正在推廣的「復興中華文化」背道而馳,遭致「查禁」的命運。《中國人的性格》所承載的「科際綜合研究」也隨之暫隱。
2014年,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又一本揭櫫科際對話,也是由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共同主編的論文集《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劉斐玟、朱瑞玲主編)出版了。兩書相隔40餘年。這一時間脈流所標誌的,既是傳承,也是國際學術典範的轉變:從宏觀的行為科學式論證,轉向微觀的個人身心感受與文化價值承載;由探詢什麼是文化,轉而思索如何進入文化。在「傳承」與「轉變」中,我們當如何思索科際合作的開展向度和對話深度?!
正是在此一學術關懷下,「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學術座談會應運而生,該座談會希望從觀照《中國人的性格》到《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的學術發展脈流,來思考如何開展科際對話的新視域。座談會邀請了四位分別代表不同世代和學科背景的學者與會:瞿海源、黃樹民、胡曉真和沈志中。在這場座談會中,他們不但促發我們反思「未來」,也帶領我們回到「過去」。瞿海源帶領大家進入1970年代的學術氛圍和篳路藍縷,並藉著張光直院士的例子,提出他個人對科際整合的思考:學者既各有專業,如何做到「道不同‧相為謀」?議題的設定如何避免「大而無當,小難集氣」的缺失?研究論著如何在學術專業和知識普及之間平衡?黃樹民則是從國內的政治局勢和國際學術潮流,來呈顯《中國人的性格》的學術文化價值:委婉地批判以意識形態來箝制學術思路的政治勢力。黃樹民並以之對比《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從中點出兩書的不同取徑,實則反映了國際學術典範的轉移:從追求實證科學、大議題的研究意識,轉向以個人為文化載體的人文取徑;從科際整合轉向科際對話。胡曉真則是以「說書」的方式,帶領大家進入她個人的治學經驗,以及中研院文哲所作為一個多學科的學術機構如何在「各別發展」和「對話合作」中建立浮動平衡。她所提出跨學科研究的「背景」vs.「前景」,頗具啟發性;她同時也以文學詮釋為例,表達出她對深化跨學科對話的關懷與期許,並點出「意志力」在科際對話過程中的重要性。沈志中更縱橫古今,從哲學家蘇格拉底到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巴夫洛夫,乃至英國文豪愛倫坡,以此點出個人內心世界的複雜性,以及反求諸己、以他人為師、協力探索等對話觀點和研究反思。
時值李亦園逝世週年,為追憶之,謹將這場學術座談會整理成文,以此向李亦園等引領科際綜合研究、建立科際對話器識的先輩們致敬,特別是他們進行科際合作時所展現的學術典範以至誠之心面對知識,以謙和的包容力對談學術。
哲人雖已遠,典型在夙昔。
追憶李亦園院士: 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科際綜合研究」的舵手 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https://bit.ly/3jhFJ5I
國家圖書館 期刊文獻資訊網 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系統:進階查詢
2017年4月18日19時,著名人類學家、中研院李亦園院士於臺北醫學院附屬醫院病逝,享年86歲。
李亦園,1931年生出生於福建省晉江縣,著名人類學家,中研院院士,人類學高級論壇創建顧問。
1948年就讀於台灣大學歷史系,後轉至考古人類學系,1953年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 1958年赴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留學,1960年獲得碩士學位。
1955年至1998年間任職於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歷任助理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其間並於1968年至1977年擔任副所長、所長,並曾任總幹事、評議員、諮詢總會常務委員等院內職務。
1968年至1983年擔任臺灣大學合聘副教授、教授,後擔任校聘講座教授。 1984年獲選為中研院院士,同年創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並擔任院長共6年。
李亦園先生是國際著名人類學家,育才無數,著作等身,研究領域包括人類學、文化理論、家族組織、比較宗教、儀式象徵、神話傳說等,其著作有《文化的圖像》、《人類的視野》及《田野圖像》、《文化與行為》、《信仰與文化》等專書十八種,專業論文一百三十余篇,他以四十年實地田野研究,創建一套中國傳統民間文化理論,廣受學界推崇。
除了學術研究之外,李亦園先生也多方參與行政與教學工作,並經常對當前社會與文化問題撰文發表想法,是位將所學與社會密切結合的學者。 不論在學術研究上或是社會文化方面,均可見其卓著的成就與貢獻。
2002年起,擔任中國人類學高級論壇首席顧問。
2017年4月18日19時,在臺北醫學院附屬醫院病逝,享年86歲。
李亦園先生著作。
一、專著。
[1]李亦園(1966)。 文化與行為,臺北市:台灣商務。 。
[2]李亦園(1970)。 一個移殖的巿鎮:馬來亞華人巿鎮生活的調查研究,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3]李亦園(1978)。 信仰與文化,臺北市:巨流。 。
[4]李亦園(1983)。 師徒‧神話及其他,臺北市:正中書局。 。
[5]李亦園(1982)。 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市:聯經。 。
[6]李亦園(1984)。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臺北市:水牛圖書。 。
[7]李亦園(1992)。 文化的圖像(上):文化發展的人類學探討,臺北市:允晨文化。 。
[8]李亦園(1992)。 文化的圖像(下):宗教與族群的文化觀察,臺北市:允晨文化。 。
[9]李亦園(1996)。 文化與修養,臺北市:幼獅。 。
[10]李亦園(1996)。 人類的視野,上海市:上海文藝。 。
[11]李亦園(1999)。 田野圖像:我的人類學研究生涯,濟南:山東畫報。 。
[12]李亦園(2004)。 宗教與神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13]李亦園(2002)。 李亦園自選集,上海市:上海教育出版社。 。
[14]李亦園(2003)。 說文化,談宗教:人類學的觀點,臺北市:台灣大學。 。
二、合著。
[1]李亦園、徐人仁、宋龍生、吳燕和(1963)。 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2]李亦園、文崇一、葉啟政、楊國樞、馬漢寶、張春興等(1982)。 握緊自己的方向盤,臺北市:正中書局。 。
[3]李亦園、戎撫天、王維蘭、吳燕和、謝劍(1985)。 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臺北市:正中書局。 。
[4]李亦園等著。 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1962),臺北市: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 。
唁電。
中研院並轉李亦園先生親屬:
驚聞著名人類學家、中研院院士、人類學高級論壇創建顧問李亦園先生不幸於2017年4月18日逝世。 噩耗傳來,我論壇全體同仁萬分悲痛。 謹對李亦園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親切慰問。
李亦園先生是國際著名的人類學家。 他淵博的專業知識,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自覺的責任意識,享譽國際學界。 多年來,李先生一直為中國人類學學科的重建和發展,殫心竭慮,運籌帷幄,身體力行,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2002年李先生又和費孝通先生等學界前輩一道鼎力支持內地和港澳台學界創建"人類學高級論壇"並擔任顧問,後又數次蒞臨論壇學術年會,為論壇的發展壯大,海峽兩岸學界的互動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李亦園先生的不幸逝世,是海峽兩岸人類學界的重大損失,我們也永失一位和藹可親、知識淵博、著作等身的導師。
李亦園先生千古!
人類學高級論壇秘書處。
人類學高級論壇學術委員會。
人類學高級論壇青年學術委員會。
2017年4月19日。 【学术资讯】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院士逝世 - 人类学乾坤

數典編號: FW_0072665 調查人員李亦園(右)與巫婆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
標題: 調查人員李亦園(右)與巫婆
描述: 原始影像記載為:李亦園與巫婆
族群: 泰雅族
資料集: 田野照片
採集時間: 1963
採集地點: 宜蘭縣南澳鄉
典藏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
管理者: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
實體典藏編號: T0373 調查人員李亦園(右)與巫婆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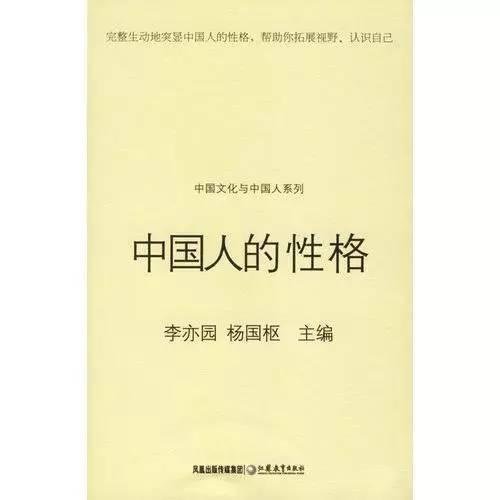


李亦園先生和費孝通先生合影
2017年4月18日,著名人類學家李亦園先生在台北病逝,享年86歲。李亦園先生研究範圍極廣,涉及人類學、文化學、比較宗教學、家庭宗族研究、神話研究,並以台灣高山族、華僑社會以及華南、台灣漢族民間文化為田野研究對象。著有《人類的視野》、《文化的圖像》、《文化與行為》、《信仰與文化》等專著16種,專業論文一百三十餘篇,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人類學者。
原文:《懷念李亦園先生》
作者:趙旭東
2017年5月21日,台灣人類學家李亦園院士告別儀式,圖片轉發自台灣「中研院」余安邦研究員。
以人類學為自立之本
四月十八日是李亦園先生的祭日,在2017年這一天,他悄然離開了這個他曾經為之奮鬥的世界。對於一位人類學家而言,死亡從來都意味著一種分離,文化從來都不會缺失一種對於亡者的悼念,葬禮儀式讓故去之人能夠在生者眼中並不孤單地安渡到另外一個世界中去。而所有活著人的悼念都是在表達這樣一種從生到死的過渡,希望借這篇小文,恭祝先生安渡金橋,抵達一個理想的彼岸世界。
記得大約二十年的夏天,北京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召開第二屆人類學高級研討班,在那個會上費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覺」這一概念,對此一點,至今人們都難以忘懷,甚至可以說,「文化自覺」的觀念已經深度影響到了今天中國的文化話語的表述。恰是在這次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有似英國式「席明納」的高級研討班上,我有幸第一次見到那時已經是「中研院」院士的李亦園先生,聽他與費孝通同席而坐,宣講他的有關於中國文化的內聖外王、天人合一以及「致中和」的諸多新解釋。儘管有許多的細節早已隨著人生無情的遺忘能力而消失殆盡了,但是他講座中間對於大陸簡體字的不理解卻一直都沒有能夠在我的腦海中被忘記掉。
他說話很乾脆,聲音也很洪亮,儘管帶著一些閩南口音,我還是清楚的記憶下來,從來不曾忘記過。他說他那個名字「李亦園」的「園」字被簡化成「園」字,一下子名字就變成是一元錢的「元」字了。
這雖屬於是一種笑談,卻無意中隱含著對他對於源遠流長的文字文化的被隨意更改的一種極度的惋惜!這恐怕就是一種人類學家對文化的在意和敏感,稍有一些文化上的變動,都會攪動人類學家那根敏感的神經。
文化很顯然是跟人的感受性聯繫在一起的,感受又是基於習慣而產生的,而習慣又毋庸置疑地是受著一種文化的框架所約束的。一旦離開了文化,習慣就會發生一種改變以及重新的適應,而缺失了某一種文化的身體感受性也就會變得令人不知所措了!
李亦園先生祖居閩南泉州,後遷居台北,求學於哈佛大學,任職於「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從所長到院士,以八十六歲高齡辭世,一生都以人類學、民族學為其立身之本,著作影響有目共睹,在這裡毋庸過多贅述,我想他的諸多弟子們會在在未來有個完整的梳理和呈現,在這方面,「執弟子之禮」,李門弟子應該是當仁不讓的。
我與李先生的機緣也僅限於那次在高研班上的會面,後來再少見到李先生來大陸,即便有一次開會去了台灣諸地,匆忙之間也難得有機會登門拜見。我關於李先生的很多信息也是從他的學生們口中了解到的。記得是在2015年的夏天,徐傑舜、周大鳴教授牽頭的人類學高級論壇學術委員會曾以「海峽兩岸人類學高級研討班」的名義組織大家去新竹的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開會,這個學院是李亦園先生所親自創立的。
還記得在人文學院一進門處擺放著的一葉扁舟,那是當地漁民生活中的舊物,擺在這裡作為人類學博物館的一個標誌性象徵物。這個學院李先生曾任創院院長,並在這裡開闢了人類學專業,聽李先生的女弟子林淑蓉教授曾經介紹過,以前這裡還有李先生的專門辦公室,偶爾他也會來新竹小住,後來年齡再大一些,身體也大不如前,來這裡的次數也就少了很多。誰能想到,2015年從台灣訪問回來之後,到了第二年就聽聞李先生的女弟子林淑蓉教授病逝的噩耗,許多同人為此扼腕,林女士做事情的認真和執著絕不亞於他的授業恩師,真可謂「虎門無犬子」,中國的這句成語最為生動地描述出了這一點。
李亦園先生著作《文化與修養》
在我看來,李先生的人類學無疑是代表一個時代的。他在台灣「中研院」民族所的持久經營為社會與文化人類學在這裡的開花結果營造出了一片享譽世界的天地,在那裡人類學有著自己獨立的地位,它與民族學、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等社會科學學科並駕齊驅,一派多元包容的景象,可惜後來李先生卸任民族所所長之後,一本很好的《民族學集刊》被改了名字,叫《台灣人類學》,不論改名字背後的政治或者經濟的原因如何的不可言說,但是這樣一改,似乎完完全全失去了人類學本該有的包容性了。不過對此,我只是聽到風聞而已,孰是孰非大概只能是由後人來評說了。但我心目中的那本集刊仍舊還是一本上乘的漢語學術刊物,它樸實無華,專於學術,富含多種的啟發性。
《中國人的性格》
人類學可謂是對人類整體的研究,注重人類的社會與文化的表達。人類學很顯然不可局限在某一個地區甚至是某一個國家之內,人類學命定是要求要有一種全球、全人類的關懷的,它當然可以基於一種本位文化意識的全球關懷,而非必然局限於自身本位文化的偏於一隅的獨自構建和自我欣賞。
李亦園先生和費孝通先生合影
大約是在1997年的夏天,李先生和費先生之間曾經有過一次今天看來屬於世紀性對談的一次對話,對於中國人類學的發展而言,這可謂是富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次對談。今天依舊值得去細讀對談的內容!甚至費孝通和李亦園二位先生之間的那次對談可以看成有關中國本土學術自覺的一個開端,在對談中,他們深度地觸及到了一種帶有共同性意識的中國本位文化的思考,即什麼究竟是中國文化,什麼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特徵,如何可能構建起一種中國問題意識下的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理解?所有這些都在這場對談中被提起並得到了一種初步的回答,影響極為深遠。今天世界性的文化接觸,重新又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考問著後來者的智慧、膽識和能力。
李亦園先生成就了一代中國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促進了海峽兩岸人類學與民族學之間的廣泛交流,並以其獨有的學問和睿智回饋於他的故土,推動了大陸人類學的重建與自我提升,相互之間的聯繫和往來在李先生的引領下可謂緻密、頻繁且成果頗豐。由此而猛然想起《詩經·淇粵》的古句:「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壁,寬兮綽兮」。或許,最後以此形容李亦園先生學問人生並不為過。海天阻隔,不能親到先生靈前拜祭,遙祝先生一路走好!更期待先生用一生所鋪墊的兩岸人類學、民族學順暢交流之路可以越走越寬廣。
(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晨寫於南書房)
文章發表於社會科學報微信公眾平台,紙媒即將刊發,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長按二維碼關注
做優質的思想產品
社會科學報
「以人類學為立身之本」:李亦園先生告別儀式今日舉行社會科學報 - 每日頭條 https://bit.ly/3m4Uxq6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ulture/z3xy4gp.html
李亦園 。 寂寞的人類學生涯。
2019-07-11 18:14。
李亦園。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喬健教授是我在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學弟,他晚我幾年進入人類學的領域。 人類學是一門冷門學科,系裡的學生非常少,所以喬健兄說他在校時是一班一個人形影孤單地唱獨角戲唱到畢業,而我就讀的這一班(考古人類學系第一班)也比他好不了多少,連我只有二個人,雖不至於形半影孤,但也是十分冷清。 我們本學校時常常說我們這一班開班會每次都全到,畢業后則開班友會每次都全到(因為只要有一人不能來就不開)。 不過,現在我們永遠無法再召開班會了,因為我的惟一同班同學唐美君教授(考古人類學系第四任系主任)已於1983年逝世了,所以我也和喬健教授這一班一樣,永遠是形單影孤了。
學人類學的人不但在學校裡十分孤單寂寞,畢業後去做田野工作更是寂寞。 人類學的研究工作有一大特色,那就是要到研究的地方去做深入的調查探索,無論是蠻荒異域或者是窮鄉僻壤都要去住過一年半載,並美其名叫"參與觀察",認為只有這樣長時間地深入於其中,才能真正徹底地瞭解你所研究社群的實情。 但是在那樣的蠻荒或偏遠地區而又人生地不熟之處,一個人單槍匹馬要去住一年半載,不但孤單寂寞,而且甚至於危險萬分並有生命危險,所以喬鍵兄在描述他的拿瓦侯印第安(Navajo Indian)村落之行時就說到土著懷疑他是間諜,並立揚言要殺掉他。 在講到探訪廣西省的瑤族時,也說到30年代著名的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也就是在此地調查時出事,其夫人王同惠女士因而遇難的故事。 可見人類學者的田野工作的確是十分辛苦而寂寞的。 我自己早年在高山族的泰雅族中做研究,曾走了兩整天才到達一個叫金洋的小村落,在那裡前後住了數月,寄信國家時郵票被偷掉了,家中和研究所的同事們急得不得了,以為出了什麼事。 另一次去砂勞越做調查的時候,一個人沿拉讓河(Rajiang River)而上去住在達雅人的長度里,回想起他們從前是獵頭民族,半夜裡有時聽到鼓盧也不免心驚。 著名的英國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B.Malinowski)是長期田野工作的創始者,他在大平洋的小島初步蘭群島(Trobriand Is.) 做研究,前後住了快四年。 在那種蠻荒孤島上一個人住了那麼久,有時候煩躁起來真是要發瘋,所以馬氏在他私人日記中有時竟會詛咒那些他原本很心愛的初步蘭土著。 他死後其夫人將日記出版,立即引起人類學界的一些風波。 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人總是人,人類學家在田野一久,總不免有些牢騷,那就是源之於長久的寂寞之故。
費孝通與王同惠結婚照。
但是人類學家為什麼要這樣自我放逐似的去備嘗田野的孤單寂寞呢? 那是因為田野調查實在有其吸引人之處,尤其是面對異民族文化之時,所引起的那種文化衝擊或文化震撼,經常是使你終身難忘,甚至於刻骨銘心。 喬健兄的這本"田野筆記",就是把他30年來在北美洲、中國大陸做田野時所遇到的種種震撼,以及辛苦與寂寞,以輕鬆的筆法寫下,娓娓道來,至為生動感人,不但可吸引並滿足一般讀者的好奇之心,而且連我這老田野也為之心動不已。
喬健兄的田野經驗比我廣闊,早年我們同樣是以研究高山族出家,後來我做華僑研究以及臺灣島內漢人社區的研究,但是他卻有機會跟隨他的老師John Roberts教授(也是我的老友)去跑遍了美國西南部印第安人保留區;而離開美國後,因為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教職,所以比我們更早有機會去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區域做調查研究,其經驗就更為扣人心弦, 而因此所發出來的分析與議論,甚至於對文化的種種拴釋、註解,都值得無論是專業的人或一般讀者的細心一讀。
喬健兄在寫他的第四次拿瓦侯印第安遊記時,曾說到一則拿瓦侯人調侃人類學家的笑話:「一個拿瓦侯家庭通常包括母親(他們是母系社會)、父親、子女和一個人類學家。 "這是因為人類學家很喜歡以拿瓦侯族為研究物件,所以研究者不斷進出他們的村落,拿瓦侯人覺得很不耐煩而造出了這一則笑話。 還有另一則調侃人類學家的笑話:「美國早期人類學家克魯伯(A.R.Kroeber)寫過許多有關印第安人的報告,有一次他又到一個印第安人家中去訪問,問一個報導人問題時,那人 總是要回到房間去一會兒再出來回答,克魯伯很奇怪,問他是不是到房裡去轉問他母親,那印第安人答說是去翻閱一個人類學家克魯伯的報告,以免把自己的風俗記錯了! "從這兩則笑話里我們可以看出土著民族對人類學家的複雜態度。 人類學家長久地停留在他們村落,為了要深入瞭解,所以無所不問,無所不談,真的常常是打破砂鍋問到底。 記得有一次我的助手四度去訪問一位村中的婦女,前三次都被拒絕了,第四度再去時勉強接受了,但脫口而出的話是:"你怎麼這樣陰魂不散啊! "人類學家不僅寂寞孤單地做田野,而且隨時有遭白眼或調侃的機會,所以喬博士在拿瓦侯區調查時,拿瓦侯人會對他說:"你的研究對你有好處,對我們卻沒有好處。 "你是從那麻煩最多的地區來的,我們怎能信任你呢?!"
臺灣泰雅族人。
其實,人類學家做研究,有時並不一定對自己有好處,他也不一定在意於是否能對自己有好處,但是心中所想的卻大半是如何對土著或被研究的人有一些好處。 就如我們前面所說的,人類學家長久時間地做參與觀察,其目的就是希望能瞭解上著內心的所思所好,藉以從他們自己的立場出發,向世人說明他們的文化、狀況與心理趨向,以免文明人城市人錯解了他們的心意,而把自己之所愛硬安到別人的身上,而且自以為是"人道主義"。 比如說,從前有一位大官到蘭嶼去視察,看到雅美族人所居住的半地下屋以為是落後貧窮,有礙觀瞻,所以下令替雅美人蓋了一排排的鋼湯水泥"國民住宅",沒想到這些"現代化"的住宅都不為土著所喜愛,一間間變成養豬的屋子。 這位大官沒有上過喬博士的人類學課程也沒有人給他有關臺灣高山族的知識,所以他不知道雅美族人的居住房屋構造有適應地理環境、調適氣候、表現社會地位等種種功能,而且他們的房屋組合也分住屋、工作足、涼亭、船屋等類別,不是簡單的一小間鋼筋水泥屋就可解決事情的。 又如前些時候花蓮山地雛妓的事間得很熱,大家都為土著少女的遭遇而歎息同情,但是一般人心中總留了一種說不出來的疑問:"山地女孩總是比較隨便吧! "其實這想法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一種大漢沙文主義在作祟,因為就以花蓮泰雅族為例,他們固有的貞操觀念有時還比我們漢族更嚴格! 還有更可笑的是前兩年行政單位受了「復興中華文化」的影響,要在山地各民族推行做族譜,他們腦子中以為所有的民族都像漢族一樣有父系家族氏族制,而不知道高山族中有好幾族都是"雙系"或"無繫"的親族組織,如要做族譜則四代以上就有16個譜系,這如何做法連我們這些譜牒行家也想不出來! 人類學家就是這樣站在土著文化的立場為他們說話,為他們的處境與內心思維作闡釋,並企圖扮演他們的代言人,但也因此而犯了行政當局之忌,不為他們所喜歡,甚而說我們是偏袒少數民族。 人類學家對少數民族的心結就是這樣複雜而糾纏,我們覺得他們是少數,所以意見常被忽略,所思所想常被抹殺,利益常被忽視,現象常被誤解,所以經常要為他們說話,為他們爭取權益。 我們不但為文化上的少數民族或弱勢群體(Cultural Minority)而說話,我們也為社會上的其他少數或弱勢群體(Social Minority),如女性、老人、少數宗教團體、殘障者等說話,併為他們爭權益,因此常常就會被誤會是異議分子,甚至被祝為吃裡杠外,併為行政當局所不喜歡;學術主管嫌我們愛管閒事,或說我們不務正業。 ;行政主管怕我們抬出"憲法"、"部落公約"等等來找他們麻煩,所以厭惡之至而避之惟恐不及。 人類學家就是這樣不自討好的人,寧願形單影孤地到蠻荒之地過寂寞生活,做研究時土著對你不耐煩,威脅要驅逐你,做完研究寫成報告後行政主管們又討厭你詛咒你,難道人類學家真的喜歡這樣的寂寞生涯嗎?
其實人類學家並非真的是喜歡寂寞生涯,人類學家之所以樂於奔走於蠻荒之地,忍受土著的不耐與行政人員的譏諷,原也只是為了一種信念,一種遙遠的理想在鞭策著他,就如喬健兄在書中《漂泊中的永恆》一篇所描述瑤族人追尋他們的千家峒一樣,人類學家只是在追尋他們對人類永恆本質的信念。 瑤族人在元成宗大德九年,也就是西元1305年3月19日,元兵攻入湘西的千家峒老家,他們的祖先棄峒而四散逃走,並把原來供奉的神祗埋在地下,乃發願五百年後子孫再回來相聚朝拜。 千家峒原是一個瑤族人像陶淵明詩中所描述的桃花源那樣的人間樂上,這代表瑤族人對固有文化及其發源地的一種懷念之情。 這種人間樂土的懷念之情經過傳說沿誦以及儀式扮演,不但久已成為瑤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形成類似人類學典籍中所描寫的「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或「復振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或者像基督教中的千年福崇拜*(Millenarianism),追尋天國復臨之福一樣, 他們不斷地要找到千家峒老家。 喬健兄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重返千家峒的運動在近代不斷發生,1941年廣西大瑤山地區的盤瑤盛傳千家峒出了盤王要帶瑤族回去。 這午農曆八月初一大批瑤民聚集在廣西忠良縣山界村,敲鑼打鼓地出發往千家峒,當地政府以為瑤人造反,派兵鎮壓,並把幾個帶頭的人抓起來。 1957年廣西岩城的瑤人傳說在湖南找到千家峒...... 消息傳布開來,迅速形成一大規模的千家峒運動。 但不久反右運動開始,(主事人)周先隆被打為'地方民族主義'及'現行反革命',判刑15年! "
永州江永千家峒。
這種的故事在人類學文獻中極為熟識,而在臺灣我們也很容易者到類似的例子,基督教中的一個新教派,傳言在中東的聖山"錫安"(Zion)已"遷"來臺灣南部,於是形成一股朝聖熱潮,最後行政當局懷疑他們要"造反",終於派人取締他們。 這種對遙遠理想之國的追尋,應是人類的共同現象,在宗教活動中層出不斷,在受壓迫的少數族群中更是此起彼落,在知識追求的領域內,對於理想範式(Paradigm)的追尋也不斷 翻新,人類學家執著於人性普同本質與文化歧異的追尋,就像瑤民的千家峒尋根,或是基督徒的找尋天國復臨的運動一樣,忍受寂寞與困難,鍥而不捨去追求他的理想。 然而他與宗教徒或少數族群也有不同之處,他們用理性與科學,而不用傳說或巫術,去追求理想之國,所以其歷程雖然寂寞,但是理想之國終會有一天到臨的。
李亦園。
寫於1990年6月23日颱風之夜。
此文為李亦園先生為喬健先生著作《漂泊中的永恆——人類學田野調查筆記》一書寫的序。
《漂泊中的永恆——人類學田野調查筆記》(喬健 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




泉州籍人類學大師李亦園逝世 系「泉州學」奠基人
泉州籍人類學大師李亦園逝世 系「泉州學」奠基人 - 每日頭條 https://bit.ly/2FLtFvK
泉州網4月21日訊(記者 許奕梅 文/圖)「深切悼念泉州籍著名學者李亦園先生。」4月19日下午,泉州學研究所所長林少川在朋友圈發布李亦園辭世的消息,給泉州文學界帶來不小的震動。昨日,泉州市政府代表家鄉民眾,向李亦園先生治喪辦發去唁電,向其親屬表示慰問。
李亦園,福建泉州人,1931年出生,1948年赴台,從事人類學研究至今,是人類學研究的代表性大家。而近三十年來,他以泉州鄉親和台灣文化使者的雙重身份,活躍於泉台文化學術交流的舞台,對「泉州學」的確立、構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為最早推動兩岸多領域學術交流的學者之一。
李亦園李少園這對「海峽兄弟」2012年相會於台北,同年,《李亦園與泉州學》出版。(黃帆/攝)
李老先生(右)為泉州學研究所題詞
他與故鄉的情懷
時隔38年與母親重逢 他跪行40餘步
1948年秋,17歲的少年李亦園在晉江古渡頭,拜別依依送行的母親前往台灣就學。豈料人為藩籬,山海阻隔,此一去40多年山重水隔,母子無緣見面。
在熟識的人眼中,這位貢獻卓著的學者內心,始終割捨不下對家鄉和親人深深的眷戀。「身為遊子,李亦園先生懷有濃厚的家國情懷。」泉州紀錄片導演陳家平回憶道。
李亦園的胞弟李少園曾是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家平作為他的學生,有幸聆聽了李亦園老先生的故事,之後趁赴台工作之際,為李亦園創作了一部紀錄片《故土情緣》。陳家平介紹,拍攝期間參觀了李亦園創辦的人類學研究院,整個建築裝修得如同泉州古大厝,讓人備感親切,也透出這位曾經只能隔海望鄉的學者對泉州故鄉的眷戀。
在採訪李亦園時,陳家平得知,李亦園在與母親分別了38年後,於1986年在香港機場與母親重逢。那一刻,李亦園跪行40餘步與母親抱頭痛哭,用淚水傾訴骨肉分離近半個世紀的思念之情。
直到1989年,李亦園第一次回大陸看望89歲高齡的母親。李亦園曾回憶道:「1989年的中秋之夜是我們全家最高興的夜晚,89歲的老母親苦苦等了我40多年,終於等到我回家團聚。結果我僅陪伴她4年,她就逝世了。」
愛用閩南語吟詩 喜吃泉州綠豆餅
「伯父臨終前語:『阿母帶吾去也』,遂安詳而逝。」在接到伯父辭世消息的電話時,李亦園的侄兒李可丹哽咽失聲。
李可丹上大學時,在香港中文大學初見來講學的伯父,就被他的傳統文人風骨與儒雅氣質所折服。此後多年裡,李可丹的父親李少園、姑姑李園生也多次到台灣和伯父一家團聚。「每次過去,伯父都讓我們帶綠豆餅去給他吃。」李可丹說,在台灣生活多年,伯父還是最喜歡泉州的特色小吃。「每次去看望伯父,他就喜歡用閩南語和親人們交流,而他最愛用閩南語吟誦古詩,聽來饒有韻味。」
2003年中秋節,李亦園和弟弟李少園在泉州故居團聚賞月,李亦園望著天上的明月感慨道:「去時17歲,回來71歲。月是故鄉明,餅亦故鄉香。回家的感覺真好!」「那時他的話把大家都逗樂了。」林少川說。
他對家鄉的貢獻
他是「泉州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剛聽到李亦園先生辭世的消息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心情十分悲痛。」林少川稱,李亦園是他十分欽慕的學者,他對泉州學的學科建設和理論架構的確立有著深刻的影響。
林少川介紹,1989年李亦園首次回鄉探親時出席了學術座談會,會上他認為「提出泉州學是可以的、可行的」,由此引起泉州文史界人士的重視,並開始了創立「泉州學」的探索。1999年在「海峽兩岸泉州學研討會」上,李亦園提出對「泉州學」的見解和定義,對「泉州學」的確立、構建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2002年,李亦園在《釋論「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跡」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之內在文化意涵》論文中,運用費孝通與之談話中提出的中華文化具有「美人之美」特點的重要論述,得出了泉州人獨具「海洋心胸、海洋性格」與「寬容並納、百教共存」等文化特質,在充滿文化紛爭、宗教衝突的當前世界是值得世界各國學習的,具有真正的「普世價值」的創意性結論。2003年,李亦園再次強調了這一觀點,從大視野、大格局闡釋了「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跡」所具有的泉州文化精神,為新世紀「泉州學」研究指明了方向。
2012年,泉州學研究所與泉台交流協會一起聯合出版《李亦園與泉州學》一書,是對李亦園先生有關「泉州學」研究成果的一次匯總。
他用閩南文化來解決自己的「雙重身份」
林少川介紹,李亦園先生的故鄉情結,從他對泉州的研究程度中可見一斑。為更好地研究泉州人,他三次去往與故鄉民風、習俗相同的地區——台灣彰化縣「泉州厝」,前後住了一年半。為了解海外泉州華僑社會,他到馬來西亞南部一個永春人聚居地,一住就是一年。
李亦園還致力於促進泉台間的文化藝術交流。他運用自己在台灣的聲望和人脈,與泉州學術界進行多個項目卓有成效的合作。
熱愛故鄉的李亦園以泉州鄉親和台灣文化使者的雙重身份,活躍於泉台文化學術交流的舞台。林少川回憶,李亦園應邀回泉出席第二屆「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時,他在大會演講:「過去我曾很矛盾,主觀與客觀的矛盾。我是台灣人,也是泉州人,以往一直不知道應該如何來解決雙重身份,台灣與泉州都屬於閩南文化,現在可以用閩南文化來解決我的雙重身份。」他提出兩岸應共同努力,通過合作,研究「閩南學」
泉州籍人類學大師李亦園逝世 系「泉州學」奠基人 - 每日頭條 https://bit.ly/2FLtFvK
關於李亦園院士
李亦園李亦園先生為國際知名人類學家,育才無數,著作等身,研究領域包括文化理論、家族組織、比較宗教、儀式象徵、神話傳說等,其著作有《文化的圖像》、《人類的視野》及《田野圖像》 等專書十八種,專業論文百餘篇,他以四十年實地田野研究,創建一套中國傳統民間文化理論,廣受學界推崇。除了學術研究之外,李亦園先生也多方參與行政與教學工作,並經常對當前社會與文化問題撰文發表想法,是位將所學與社會密切結合的學者。不論在學術研究上或是社會文化方面,均可見其卓著的成就與貢獻。
1931年,李亦園先生出生於福建省晉江縣。1948年就讀台灣大學歷史系,後轉到人類學系,1953年畢業後留校任助教兩年,1958年到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進修並獲碩士學位。李亦園先生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教授,1984年創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並任院長共六年。
李亦園先生於198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89年開始擔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2001年轉任董事長。其致力於人類學研究長達40多年,更積極將漢學研究與台灣研究推廣到國際學界,榮獲法國巴黎第四(Sorbonne)大學以及澳洲 Griffith 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德國海得保大學獎章、捷克查爾斯大學特殊貢獻獎,在國際漢學界裡極具聲望,1998年並獲行政院文化獎及中華民國政府二等景星勳章。2004年,在清華大學前後任五位校長毛高文、劉兆玄、沈君山、劉炯朗以及徐遐生校長的見證下,獲頒名譽博士學位。李先生在人類學與漢學研究之貢獻與成就獲得學界高度肯定,多項殊榮,實至名歸。
李亦園(Li, Yih-yuan)【簡歷】
劉兆玄校長與李亦園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學士(1953)
美國哈佛大學碩士(1960)
法國巴黎大學(梭邦)榮譽博士
澳洲格利斐斯大學榮譽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名譽博士(2004)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博士(2005)
現職: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通信研究員( 1998.7-)
中央研究院院士(1984.12 當選)
中央研究院評議員(1984-)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諮詢委員會召集人(1991-)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教授(1987-)
經歷:
中國民族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理事長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諮議委員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1967.8-1998.7)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創院院長(1984.8-1990.7)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1971.10-1977.10)
美國匹茨堡大學人類學系訪問教授(1980.9-1981.7)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所長(1968.3-1971.10)
中央研究院代總幹事(1968.3- 1971.10)
國立台灣大學教授(1967.8-1984.7)
國立台灣大學副教授(1961.9)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1960.7-1967.8)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57.7-1960.6)
中央研究院助理(1955.7-1957.6)
國立台灣大學助教(1953.9-1955.7) 李亦園院士捐贈手稿專著暨手稿展:簡介
李亦園院士捐贈手稿專著暨手稿展:簡介 https://bit.ly/35lhXR9




李亦園 補了人類學缺塊
黃進興 2020年03月01日 06:00
封面故事李亦園 補了人類學缺塊 - 世界新聞網 https://bit.ly/2IQslZP
鄭重聲明 本篇內容為世界日報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任意轉載、重製、複印使用。
甫進台大歷史系,頭一年必須修習「人類學導論」,該門課係由人類學系的先生輪流就各專題做講演;居中李亦園(1931—2017)老師的授課,最為生動有趣,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於考試成績出乎意外的好,曾姓助教還來問我是否要轉系,可是因為和歷史系諸位同學已經有了不解之緣,只好決定留在本系。但受此鼓勵,之後又去旁聽了李老師的「原始宗教」、「人類學方法論」,受益更多。即使到哈佛進修,也一直保持這方面的興趣,常到人類學系旁聽課。日後,我會特別關心儒教的宗教面相,恐怕其來有故。
台灣人類學先驅
要之,1970、80年代,李老師風華正盛,與楊國樞(1932—2018)幾位教授戮力行為科學本土化,厥功至偉。合著的《中國人的性格》成為見證時代的學術著作,廣受好評,學生幾致人手一冊。李老師遂因緣際會成為本土人類學的代表人物,備受推崇。其實李老師治學十分開闊,舉凡南島原住民、漢人社會和海外華僑均有所著墨,真是名副其實「中外兼修」的博雅學者。
由於李亦園老師兼備學問與行政之長,聲名在外,1984年,遂受命籌設新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出任創院院長。後來「歷史研究所」因人事的紛擾,所長懸缺;有天他竟出面力邀資歷甚淺的我擔任所長,委實讓我受寵若驚了。但我慮及剛返台不久,人生地不熟,諸事未備,也就婉拒了他的好意。李老師難免些微失望,但仍囑咐我留在歷史所兼課。再有機會和他接觸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
李老師是位美食家。1989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成立,他復受邀擔任首屆執行長;辦公室位於敦化南路,午間休息,他喜歡自己附近閒逛,找個小館子,打牙祭。有次,內人和我剛好路過,巧遇李老師,便拉去一齊用餐,言談之間,備極關懷。其實,李老師一貫對待學生和晚輩十分呵護,就是如此。據告,臨終前數日,有幾位老學生去看他,還一再叮囑著要家人掏錢,請學生去用餐。以我個人為例,老師往生之後,有天前去探望師母。師母隨手取來一個預置的牛皮紙袋,內放有一方極精緻的瓷製硯台,謂李老師想留給我作為紀念,頓時百感交集心茫然,蓋老師不知不文的我乃是書法的門外漢!
推掉中研院要職
眾所周知,李老師為台灣人類學界育才無數。此外,我總覺得李老師對史語所「情有獨鍾」,也先後提攜了不少歷史同仁(例如邢義田、王汎森、王明珂等)。首先, 史語所的創辦人--傅斯年(1896—1950)先生恰是他就讀台大時的校長,對李老師愛護有加,因為李老師當時患有肺病,傅校長特別替他每餐加個雞蛋,這在那個兵荒馬亂、物質極度匱乏的時代,不可不謂惜才之舉。而李老師又曾在歷史系唸了兩年,方才轉至始創立的考古人類學系就讀。或許這些緣故,令他始終關注史語所的發展,每每交談,即詢問史語所上上下下的狀況。
有件事容值一提:有天夜深幾許(記得將近10時),李老師突來電寒舍,邀我去他家,謂有要事相商;讓身為小輩的我,甚感意外。原來李遠哲院長有意延攬他出任中研院人文副院長。當時李老師身兼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忙於建樹,取捨之間,頗感為難。我雖然建議老師予以接受,到中研院一展長才,但他顧慮立法院問政的生態,終究未能應允。不免影響了中研院人文領域未來的走向。
就私人而言,我之當選院士,李老師鼓勵最多。因為自己深怕落得古人所謂「困於場屋」的衰事,有點怯場;但禁不住李老師再三的勸勉和舉薦,最終不負老師的期望,勉強忝列其間。之間,卻發生了一樁頗為尷尬之事:2006年,李老師估計我應會膺選院士,遂將數代相傳的《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錄》事先題了字,作為慶賀。不料,我又落選了。但是他老人家還是把我找到家裡,將那本原為名考古學家梁思永(1904—1954)先生所傳承的《院士錄》送給我,以為打氣。我卻因禍得福,獲此至寶。
談學術忘記病痛
因我自幼體弱多病,醫療之事,不得已略知一二。李老師晚年稍有病痛,即電傳我諮詢,尤其受封「首席醫療顧問」之後,過從更密。後來李老師因心臟病之故,動了大刀,甚傷元氣,精神亦大不如前。視茫耳聾,備受煎熬。眼看他飽受身體衰微之痛,心裡也暗自難過。每回下班無事,即順道前去探望,李老師始則唉聲嘆氣,惟一旦話及陳年往事、學術佳作,則神采奕奕,幾乎忘記病痛一事。我則成為他最忠實的聽眾。
居間,他與前輩費孝通(1910—2005)先生晚年相知相惜的情誼,是我最喜歡傾聽的際遇。緣於費先生於文革時期,對外面人類學的發展較為隔閡,李老師的學思經歷恰好補上這個缺塊。
但不可諱言,李老師為台灣人類學的發展確實憂心忡忡,亟怕青黃不接,後繼無人。又,當今人類學的走向,講究的是「反思」,對「田野工作」的基本功反而看輕了。李老師對此一流弊,感慨再三。因此,但願李老師一生心之所繫的民族所,得結合兩者之長,有朝一日,再攀學術巔峰
封面故事李亦園 補了人類學缺塊 - 世界新聞網 https://bit.ly/2IQslZ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