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死--不被恩准的殉死是受到嚴厲禁止的行為,被稱之為“犬死”。不能因為一點小事就白白死掉--當活則活當死則死--以背向敵武士之恥
日本人的--家,日本傳統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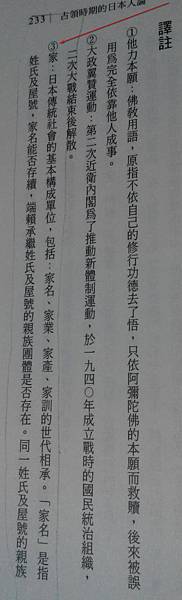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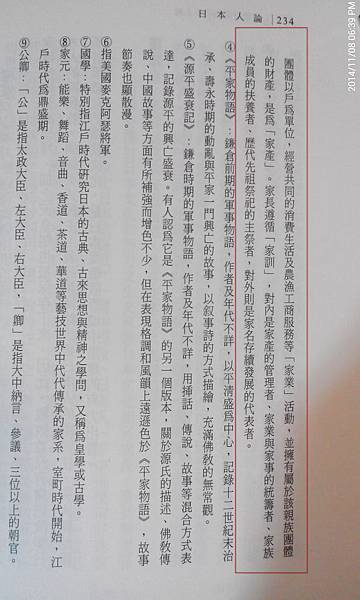
日本式的企業組織則承襲其傳統「家」制度所特有的經濟共同體觀念和垂直的「親分子分」之結構特質
------------------------------------------------------------------
日本的“家”制度和文化結構
中根千枝的集團模式理論把日本社會看做是一個按縱向序列組織起來的集團,認為處於組織頂端的,乃是一個家族主義式的領導人,集團成員之間的協調合作乃是最高的品德,以至於這樣的社會集團浸潤在家族主義的溫情神話裡。就像中根千枝指出的那樣,“滲透在日本社會各個角落的、帶有普遍性的、傳統的‘家(ie)’概念就明顯地表徵了這種潛在地植根於日本社會中的特殊的集團認知方式。”換言之,日本社會集團的結構原理是以日本傳統的“家(ie)”制度為基本模型的。儘管隨著日本的近代化,特別是戰後新憲法的誕生,傳統的家庭制度已經解體,甚至被視為封建的道德規範受到口誅筆伐,但卻在作為社會集團的本質性結構上深深影響著日本現代社會。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日本企業等社會集團的結構上,甚至還體現在日本整個社會的結構上。在這一章裡,我們將通過分析日本的“家(ie)”制度及其文化結構,來探討日本“家(ie)”制度與日本近代化、企業制度和家族國家等的關係。
@@由血緣與性組合起來的共同體
所謂的家庭乃是由血緣和性作為紐帶的生活共同體。由血緣聯繫起來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以及由性組合在一起的夫婦,這些成員所組成的共同體就是家庭。家庭是最基本的社會形態。家庭帶給人的,不僅是物質性的生存,還有精神上的安定感。也正因為家庭擔負著永遠保障成員們精神安定和物質安定的義務,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家庭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它自身乃是一個“為了成員們而建立的勞動組織”。對於家庭來說,家的安定和永續就成了最大的祈願。家庭的職責就是強化和履行自身的生活保障機能。
@@家的永續與“養子,制度”
如前所述,保障家庭永續性的最重要條件,乃是對血緣的尊重。血緣意味著一種永遠的延續。可是,如果只尊重生物學意義上的血緣的純正性,有時不免會出現血緣的斷層。於是,在日本就對血緣進行了擴張解釋,即便在生物學上沒有血緣關係,但只要辦理了養子手續,那麼在社會上也就被視為血緣得到了延續。
養子分為兩種,一種是以繼承家業為目的的養子,日語叫“相續養子”;一種是以幼兒為對像,以養育為目的的養子。作為前者,是在沒有子嗣,但有親生女兒的情況下,招女婿人贅。而在沒有親生女兒的情況下,也可以招人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當養子,這在日語中叫做“夫婦養子”,即夫妻倆都是養子。與此相對,即便有親生兒子,但如果他沒有繼承家業的能力,抑或品行不端,因而不適合經營家業的時候,可以將其廢黜,或是迫使他隱居,而將有能力的其他人收為養子委以家業。
日本京都是一個古老的都城。在這兒有多達近1000家百年老字號傳統商鋪。只要看看其經營上的家訓,就可以知道他們家業長盛不衰的原點何在了。家訓的頭條總是離不開對經營者的告誡:廢黜懶散放浪的戶主。
比如,安田多七家是京都一家批發京吳服的老鋪。在《多七傳》中有明文規定:“繼承吾家者,若狂痴放蕩,無力繼承,則經親戚故舊之協議,給與其家產的百分之五,責令其分家,而另行選出適當之人。”
總之,京都老鋪既基於血緣者繼承的原則,又恪守廢黜不良經營者的規定,從而保障了家業長盛不衰,這也顯示了日本式血緣原理與日本式家業經營的合理性及其有效性。即是說,既尊重血緣,但又不拘泥於生物學上的純粹血統,由此產生了能力主義和業績主義。這樣一來,家業依靠能力主義和業績主義打破了血緣關係的停滯性,以謀求發展和壯大,同時家業又依靠血緣關係的穩定性而得到了維持和鞏固。美國人威廉·豪瑟認為,日本商家的永續性是依靠養子制度和分家制度等保障措施來加以實現的:
“即使在歐洲,也同樣有為保持延續性而做出努力的例子,但卻絕不是普遍存在的情形。在美國,只有杜邦家族、福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等著名公司屬於例外,毋寧說這樣的想法是人們感到陌生的東西。像這樣作為一般性社會規範的關於延續性的理念,在商業的世界裡,乃是日本固有的思考方式。”
這樣,家業經營,即家的生命就脫離了個人的生命,而獲得了一種超歷史性。儘管日本人也尊重血緣,但既然尊重血緣是為了家的永續,那麼,為了家的延續而在必要時將非血緣者納人血緣者中間,就是無可厚非的了。因此,為了家的延續,日本人甚至不惜和親生兒子斷絕關係,讓非親非故的他人作為養子加人血緣中,此外,還不惜和有權勢之家締結本家和分家的關係,其中包括不是血緣分家的所謂養子分家、學徒分家等等,以便根據契約來接受某個本家的庇護。除了這種家與家之間的本分家關係,還可以作為個人關係與其他人締結模擬父子關係,諸如義父義子、幹爹幹兒等等。在日本黑社會的老大與手下人之間,也締結的是一種相當於義父與義子的關係,在日語中叫“親分”和“子分”。這種社會性的血緣模擬制度,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將血緣無限地擴大。而這種特點一旦被加以意識形態化,並擴展到國家的規模上,就不難形成所謂的家族國家主義。
家如果是孤立的,就很難期待它獲得安定和永續。一旦遭到其他家庭的敵視,處於非協作關係,要想保持安定和永續是非常困難的。為避免這種局面的出現,一個家就要和其他的家建立連帶關係。其典型的例子就是由本家和分家所組成的“同族團”。如果將此概念再加以擴大化,整個村落也就可以被視為同一個家族。而在同一地緣下,人們自然容易產生同甘共苦的共同體意識,以至於相互的家庭就恍如是一種血緣關係一樣。古希臘哲學家亞裡士多德就認為,一起進行日常生活乃是家的本質。而在日本也有一種說法,叫做“吃同一鍋飯的夥伴”,這種關係常年持續,就會被視為同一家庭的成員。
事實上,這種家庭觀至今仍舊影響著日本人,以至於在日本當代的不少漫畫作品和文學作品裡都可以找到其深深的印記。比如,當紅女作家吉本芭娜娜的成名作《廚房》就是一篇與廚房密切相關的小說。吉本芭娜娜在其中所描寫的家庭遠非一般意義上的家庭。聚集在那兒的人們大都沒有血緣關係,但如果把共同生活的“居所”作為一個關鍵詞語來考慮,就可以斷言,那兒確實存在著名副其實的家庭。在吉本芭娜娜看來,每個人能否從中找到讓自己獲得安全感的居所,乃是構成家庭的首要條件。如果換作中根千枝的話來說,吉本芭娜娜所強調的“居所”不啻一種共同生活的“場所”概念。
顯然,人們常年居住在某個地方,在同一塊土地上勞作和生活,自然很容易萌生同一家人的意識。而這種血緣擴大的原理從一個村擴展到一個縣,就不難在同一個縣的縣民身上衍生出共通的秉性和意識,即日本人所謂的“縣民根性”。再進而擴展到整個國家,就形成了明治以後的家族國家體制。特別是在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呈現出末期歇斯底里癥狀,在狂熱的愛國精神鼓噪下,發展為所謂神聖的家族國家主義。
@@武士的家族秩序與日本的家族制度
所謂的家族制度,乃是將社會對家庭的要求加以體系化的東西。家庭是生活的中心,又是最基本的社會集團,同時又是一種文化結構的表現。因此,在社會生活中,家庭具有重大的意義,使社會不可能漠視家庭的存在,勢必千方百計地統制家庭,從而導致了家族制度的產生。不過,既然家族制度是社會對家庭的一種要求體系,那麼,就不可能是對現實中家族生活的原樣複製。在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下,武士階級手中掌握了政治權力,遂認為自己的家庭秩序具有最高的倫理價值,也理所當然地最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可事實上,武士階級的家庭秩序終歸只是他們那個階級的家庭秩序,與庶民階層的秩序並不相同。而且,即便同樣是庶民階層的秩序,也因職業和地域不同而各自不同。比如,柳田國男在《民俗學辭典》中就指出,戶主權(家長權)在庶民百姓那兒就不具備武士階層那樣的絕對性。還有由長男單獨繼承家長權和財產的規定,儘管在近世的武士家法中是鐵定的法則,但在庶民百姓那兒,卻可以進行選擇性繼承,不一定非長男不可,財產也可以由幾個成員來分割繼承。
儘管武士階級和庶民百姓的家庭各個不同,但明治新體制卻面臨著建立全國通行的國家制度的必要性。因為之前的德川封建體制不過是一種藩與藩的聯合體制,而明治維新則是要建立近代的國家制度,因而有必要制定統一的全國性制度。
明治民法是以武士階級的家庭秩序為藍本,加以制度化的東西。這一點對日本後來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無疑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這並不只是意味著武士階級的家庭秩序成為了一般庶民的家族生活規範,甚至還決定了整個日本的國家體制,建立起了家族國家體制和家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從某種意義上說,家庭和國家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東西。家庭是作為人的集團的最小單位,其基礎是構建在直接性的愛情關係上的。與此相對,國家是最大的集團,儘管不排斥直接性的愛情關係,但本質上卻是建立在支配與服從的權力關係之上的。然而在日本,卻將兩者等量齊觀,將國家那種支配與服從的關係解消在愛情裡,構建了所謂“義在君臣,情在父子”的意識形態。
如前所述,武士的家庭規範被明治民法所採用,作為全部國民的家庭秩序,成了生活的規範,但事實上,它並不是對武士家庭秩序的原樣照搬,而是進行了必要的取捨。因為要用它來作為明治國家體制的基礎,武士階級的家庭規範中隱藏著一顆危險的炸彈。那就是武士的抵抗權。
@@從森鷗外的《阿部一族》看武士的抵抗權
本尼迪克特在《菊花與刀》中,注意到了義理在日本人道德規範中的重要作用。義理是一系列色彩不同的責任,其中有些甚至是相互對立的。比如,“在日本的倫理中,‘義理’既意味著家臣對主君至死不渝的忠誠,同時也意味著家臣感到被主君侮辱時突然對主君產生的憎恨。”所以,在日本既有打量描寫武士以死盡忠主君的傳說,也有不少講述武士對誹謗自己的主君進行報復的故事。作為一名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敏銳地注意到了日本武士“對名譽的義理”這個重要的概念。所謂對名譽的義理就是保持人的名譽不受玷污的本分。為了洗刷自己的污名,即便是面對自己的主君,也必須實施報復,即擁有抵抗權。她舉到了有關德川幕府第一代將軍家康的無數傳說中的一個插曲:家康手下的一個家臣聽說家康譏笑他“是一個將被刺在喉嚨的魚刺鯁死的傢伙”,言下之意是說他不會莊重而體面地死去,從而覺得受到了忍無可忍的誹謗和侮辱。當時正是家康定都江戶,推行全國統一大業的緊要關頭,敵人尚未徹底清除,於是,這個家臣向敵對的諸侯表示,願意從內部放火燒毀江戶,這樣就可以盡到對名譽的“義理”,實現對家康的報復。對此,本尼迪克特指出:“‘義理’並非僅僅限於忠誠,它在某種場合也是教人叛逆的德行。”事實上,除了本尼迪克特舉出的這個典型例子外,日本的一些小說作品也生動地描寫了武士的這種抵抗權。
森鷗外是日本明治時代的文學大師,曾在歐洲留學,擔任過日本陸軍軍醫總監,創作有《舞姬》、《高懶舟》等打量的文學名著。他於1922年發表的《阿部一族》在日本是一篇膾炙人口的小說,講述的是日本中世紀肥後(即現在的熊本)藩主與阿部家族的對立,譴責了武家社會非人性的一面。事情髮端於寬永18年(公元1641年)肥後藩主細川忠利的病故。當忠利危篤之際,有19名隨從提出殉死的請求,但只有18名得到主人的恩准。在當時,不被恩准的殉死是受到嚴厲禁止的行為,被稱之為“犬死”。
可是,在這18名殉死者中間,居然沒有包括在眾人眼裏理應殉死的阿部彌一右衛門。他自幼便跟隨在主君身邊,而今已是俸祿超過千石的武家,可主君卻沒有賜予他殉死的機會。據說是因為近來主僕之間出現了齟齡的緣故。於是,不斷有風言風語傳人阿部彌一右衛門的耳朵。最終他為了證明自己絕非卑怯之人,不得不在未獲主君恩准的情況下剖腹自殺,為主君殉死,以洗刷自己的污名。在中世,殉死者的家業將由後嗣全部繼承,並得到主君家的格外厚待。但阿部彌一右衛門的遺族們卻受到了不公平的冷遇。他的嫡子權兵衛沒能繼承父親的家業,其1500石的俸祿被分別給予了阿部彌一右衛門的弟弟們。儘管合計起來,俸祿的額度與以前相同,但阿部彌一右衛門的本家卻走向了衰落,遭到眾人的白眼。
翌年3月,在忠利周年忌之際,彌一右衛門的嫡子權兵衛也獲准作為殉死者遺族,忝列其中,為作古之人燒香祈福。這時,他剪斷髮髻,發誓再也不做武士。但這被看做是藉機泄憤,污辱主君,因而被處以絞刑。作為武士,受到的處罰不是被賜予剖腹自殺,而是像盜賊一樣被絞死,這對阿部家族而言,乃是一種極大的侮辱。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那樣:“對名譽的義理也要求在受到誹謗或侮辱時有所行動,誹謗使一個人的名譽受損,必須洗刷。或者必須對毀損自己名譽的人實行報復,或者必須自殺。”於是,阿部彌一右衛門一家只能揭竿而起,以挽回武士的面子。一族人集結在他們的本家,抵抗主君的討伐,要麼戰死,要麼自盡,連女人與孩子亦未能幸免。他們那種誓死抵抗的意志乃是出於維護武士的榮譽。儘管殉死對於本人來說,意味著生命的終結,但作為家族來說,卻是一次有可能獲得再生的機會。結果,阿部一族違抗主君的意志,致使整個家族被滅絕。他們為什麼會不惜毀滅一族來捍衛武士的名譽呢?我們不禁會想,既然如此,還不如放棄武士的名譽來維持家族的延續吧?可事實上,放棄武士的名譽,家族也同樣在劫難逃。因為背負著卑怯者的污名,武士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整個家族將永劫不復。哪怕稍有風吹草動,整個家族都有可能捲人滅頂之災,而且還得背負著卑怯者的污名。所以,與其如此,毋寧保持自己的名譽,期待家族在後世能夠復活。因此,從本質上說,不管是殉死,還是反抗,都是為了達成家族的永續。
對於武士而言,保全面子,維護名譽是絕對的信條。因為從長遠來看,它意味著家族的安穩。即使現在某個成員做出犧牲,也應該讓家族延續下去。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對阿部家族的成員來說,阿部家族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就像他們之前侍奉細川家乃是為了阿部一族的延續一樣,現在不惜反抗主家來保全武士的臉面,也不啻出於同樣的目的。
如前所述,進人明治時代以後,武士的家庭秩序被確立為社會體制的基本架構。如果不封殺上述那種武士的抵抗權,對於整個國家體制而言,將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於是,當權者千方百計來解決這一矛盾。
首先,武士是不能在家族內部發動抵抗權的。在同一家族的本家和分家之間,貫穿著徹底的支配與服從的關係,分家對本家不具備抵抗權。比如,以阿部一族作為例子來說,按照主君的命令來繼承家業,即不是由本家的嫡子來全數繼承家業,而是分散給身為弟弟的各個分家,這儘管會導致本家的衰落,卻顯然對分家更為有利。可是,分家卻對整個家族決定抵抗主君的行動沒有提出任何異議,最終與本家一同戰死。
而明治國家體制是在一個宏大的規模上來解決這一問題的。那就是建立天皇制家族國家體制。在天皇制家族國家體系中,天皇家成了所有家族的總本家。而天皇作為最高的家長,受到全部國民的絕對服從。就像“義在君臣,情在父子”這句話所昭示的那樣,上述關係被比擬為父子關係。如此一來,絕對權力就披上了愛情的外衣。倘如膽敢違抗,就成了大逆不道之舉。於是,就這樣拔掉了武士家族秩序中原有的釘子,即封殺了其抵抗權。
@@天皇家族的擴大化與神社的清理合併
為了賦予這種國家體制更大的正當性,明治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合併神社。伊勢神宮原本是祭祀天皇家氏族神的地方,以前一直不允許庶民百姓前去參拜,直到鐮倉時代起,這種禁令才有所緩和,伊勢神宮遂逐漸成為一般民眾參拜的對像,特別是在中世後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以至於伊勢被視作聖地,在普通民眾中形成了所謂一生中至少要參拜一次伊勢神宮的風潮。
但我們知道,伊勢神宮本質上是祭祀天皇一家的先祖——天照大神的地方。然而明治4年(公元1871年)5月,依靠頒布;“官社以下順序定額”這一太正官布告,日本全國各地的神社均被納人了一套等級劃分的序列中。以伊勢神宮為頂點,其下依次是由宮內廳供奉幣帛的官幣社(祭祀天神皇祖之神社)、別格官幣社(祭祀對皇室有功之臣的神社)、由國庫供奉幣帛的國幣社(祭祀在國土經營上有功之神祗的神社)等官方神社,其次才是作為民間神社的府縣社、鄉社、村社等序列。而農村村落的無格社就處在了最末端的位置上。官方神社的經費均由國庫提供,而民間神社則由府縣市町村提供定期祭祀的費用。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以天皇家的氏族神神宮為金字塔尖的神社等級制度,建立起了天皇制家族國家的信仰體系。
到了明治末期,特別是明治39年(公元1906年)8月,通過頒布;社甲第16號令,公佈了政府對神社的清理方針。但由於清理神社剝奪了庶民百姓的土著信仰對像,遭到了強烈的反對。但明治政府卻一意孤行,強行實施,其結果是,全國多達19萬餘處的神社在大正元年(1912年)被銳減到12萬餘處,而在大正5年(1916年)更是減少到了11萬處。其中受到最大衝擊的是那些末端的無格神社。
至此,天皇制信仰的等級制度最終完成。伊勢神宮這個原本只是天皇家氏族神的祭祀之地,就被供奉成了家族最高的,同時也是全部日本國民的信仰對像,成了天皇制家族國家神道的象徵。現實中的天皇家原本是京都這一地域共同體的成員,可此時卻成了全部國民的信仰對像,被加以神格化,成了“雲端上的人”。
而在神社的合併清理中,普通百姓的信仰生活遭到了慘重破壞。原本庶民的信仰生活在家族中表現為祖先信仰,在村落裡表現為氏族神信仰。這種信仰誕生在庶民的具體生活中,一旦脫離了家族和村落,離開了故鄉的山水和風土,就會失卻存在的根基。但神社的清理和合併,使人們的信仰生活與故鄉的風土剝離開來,遭到破壞。村落原本是各個家庭聯合建立的共同體,而象徵著村落共同體的氏族神信仰一旦遭到破壞,即意味著村落遭到了破壞,而村落遭到破壞,也就意味著家族遭到破壞。
明治新體制就是這樣依靠破壞現實中的家族和村落,將新的家庭和以這些家庭為最小單位的天皇制家族國家進行了策略性的重新組編。如此一來,國家就成了所謂的國“家”。然而,家族國家終究不啻一種虛構,為了讓這種虛構得以成立,顯得鮮活真實,政府就不能不利用絕對暴力來強制推行這一體制,並極大地強化家族主義意識形態。
@@忠孝一致的國民教育
這一家族主義意識形態集中體現在了明治23年(1890年)的《教育勅語》裡。《教育勅語》把“忠孝一致”確定為國民教育的基本。而此前,忠孝的順序恰巧相反,即孝才是首義的道德。比如,在明治15年(1882年)元田永孚編纂的《幼學綱要》中,孝行就排列在第一,忠節排在第二。孝被看做是人倫最大的要義,而忠則把天皇與臣民的關係視同父子。對父母的孝行之心,在針對天皇時就以忠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忠與孝被並列為人倫的最大道義,即屬於無條件的義務。忠孝觀念原本是來自中國的儒教道德,但日本人卻把這些德行加以絕對化,從而背離了儒教的倫理體系。儒教並沒有把忠孝視為無條件的德行,而是設定了一種凌駕於一切之上的德作為忠孝的前提條件,這就是仁。父母必須有仁,國君也必須有仁。如果國君不仁,那麼,臣民舉行暴動來推翻其統治,就是正當的行為。國君能否永據皇位,取決於他是否施行仁政,以至於仁成了考察中國一切人倫關係的試金石。但中國儒教的這種觀念從未被日本人接受,以至於仁被排除在了倫理體系之外。於是,忠孝在日本成為了必須無條件遵守的至高無上的德行。
不過,在明治以前,忠只是武士的德行,而對於農民來說,只有孝的存在,沒有忠的存在,也沒有人向他們做出這樣的道德要求。而且從《幼學綱要》上對忠孝的排序來看,忠並沒有凌駕於孝之上,從中不難看出中國儒教的影響。因為儒教道德的基礎就是建立在孝行之上的。儘管出於發音上的方便,經常說成是“忠孝”,但忠依舊只是第二義的道德。
但在明治23年(1890年)的《教育勅語》中,卻顛倒了兩者的順序,以至於以忠為宗旨的所謂“忠孝一致”的家族國家觀貫穿了整個小學修身教科書。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戰爭末期,日本進人了超國家主義時代,家族國家觀也走向了極端,以至於孝被完全吞沒在忠的原理之下。日本文部省於昭和16年(1941年)頒布;了《臣民之道》,其中更是充斥著天皇制家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把忠視為一切。
“我等祖先輔弼歷代天皇之恢弘天業,故此,我等向天皇盡忠節之誠即是昭顯祖先遺風,此亦為孝敬父祖。在我國,離開忠,孝將不復存在,孝以忠為其根本。基於國體的忠孝一體之道理在此散發著美麗光輝。”
字裏行間都表現出忠對孝的吞併,通篇貫穿著“孝之所以為孝乃是因為忠”這一超國家主義的倫理。而當所有的價值都被“忠”吞噬之後,已經不再有私生活存在的餘地。以至於《臣民之道》宣稱:
“即便是一碗食物、一件衣裳,也並非僅僅屬於自己,縱然是遊玩之閑、睡眠之間,我等也沒有離開國家,一切皆與國家聯繫在一起。即便在私生活中也切不可忘記歸依天皇、服務國家。”
這樣一來,就連吃飯睡覺都是為了天皇。可以說國家把真善美的絕對價值全都攬人了自己的權力之下。道德、學問、藝術等所有的精神秩序都成了服務於國家的工具。對那些膽敢違抗者,國家自然要揮動所謂“愛的皮鞭”——模擬父母之愛的皮鞭。而這就是日本天皇制家族國家觀最終所要宣揚的東西。
@@家族國家體制與日本的飛速發展
當日本明治維新時,西方列強已經建立了完備的帝國主義體制。從18世紀的第二次農業革命算起,英國是經過200多年的時間才進人帝國主義階段的。相比之下,日本資本主義的起步晚了足足100年有餘,但卻在明治維新以後不到30年的時間打贏了甲午戰爭,不到40年的時間取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以迅猛之勢追趕著西方列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但日本能夠創造這種奇蹟,其秘密之一或許就在於這種家族國家體制。它之所以順利地實現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就在於當時的明治政府成功地選擇並構建了家族國家體制。
作為資本主義確立的條件,產業資本、自由勞動者和生產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建立這三大要素的準備階段被稱之為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在日本,是以明治6年(1873年)的地租改革為契機來逐漸實現資本原始積累的。政府從農民那兒收取高額的地租,將其中一部分作為支付舊武士的秩祿公債,再用一部分來充當政府經營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本。這些政府經營的企業後來被無償地給予或是低價轉讓給和政治家關係密切的商人們,即所謂的政商,從而形成了資本家。而舊武士利用秩祿公債創辦銀行,搖身變成了資本家,或是向新資本家投資,加速了資本積累的進程。顯然,日本的資本積累就是這樣由上而下地強制實施的。
在日本農村,因為實行的是長男單獨繼承製,家產不均分,全部傳給一個兒子,使家產保持完整,易於積累起農業資本。而其他的兒子有兩種選擇,一是分家另過,給嗣子打工,二是離開家鄉到城市謀生。前一種選擇導致了“本家”、“分家”的層級關係,第二種選擇則為手工業乃至城市工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來源。而為了獲得作為生產手段的機械設備,日本只能向外國購買。而進口設備的外匯,是用日本女工紡出的生絲來換取的。像日本電影《野麥嶺》等就反映了那些出身於貧農家庭的女工悲慘的境遇。顯然,日本的資本主義是靠犧牲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們的利益,才得以發展起來的。但由於不具備國內的銷售市場,如果不販賣到國外去,日本的資本主義就會面臨崩潰。但此時,西方列強對殖民地的瓜分已告一段落,於是,日本只好在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的口號下,建立起穩固的家族國家體制,在帝國主義戰爭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不用說,家族國家體制正是建立在前述那種具有擴大可能性的日本式血緣原理之上的制度。不過,與其說它是日本家族制度的一種完成,不如說是一種扭曲,是帶著時代性和政治策略性的人工產物。
@@對家族國家的矛盾情感
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的近代化其實就是家族國家體制確立的過程,直到太平洋戰爭徹底敗北,日本的近代化才宣告破產。在這一近代化的過程中,追求自由的人們對天皇制家族國家體制進行了激烈的反抗。但日本天皇制家族國家體制的原點卻是日本的家族制度,而家庭的基礎又在於成員們與父母之間的互愛關係。顯然,那時一種無法割棄的情感羈絆。在家族國家的意識形態中,對國家體制的反抗就意味著對父母恩情的忤逆。儘管忠孝一致的國家體制是日本近代才塑造出來的人工產物,但它卻強烈地壓抑著追求自由、追求愛情的人們。換句話說,日本這種扭曲的近代化殘酷地壓抑了近代個人的真正確立。
這種複雜而奇特的性質讓人們迷失了本來的敵人。或許可以從這裡找到日本近代遭受挫折的原因。比如,在明治時代作為自由民權運動鬥士而聞名遐邇的河野廣中身上就充分體現了這種復雜性。他在《河野盤州傳》(1923年)中寫道:“從三春町的川又貞藏那兒買了約翰·斯圖加特·米爾的著作,即由中村敬宇翻譯的《自由之理》。在歸途的馬背上閱讀了此書,此前受漢學、國學培養,動輒倡導攘夷的一貫思想在一朝之間發生重大革命,除忠孝之道以外,以前的所有思想都被徹底打碎……”
河野廣中沒有意識到,忠孝一致作為家族國家體制下的最高價值,正好是與自由之路背道而馳的。以至於除了“忠孝之道”,其餘全盤採納“自由之理”,就形成了河野廣中式的日本近代,而這也正是日本眾多追求自由者的共同模式,是一直持續到太平洋戰爭結束為止的日本近代的寫照。然而,在太平洋戰爭中,就連這種與“忠孝之道”加以妥協的“自由之理”也遭到了家族國家的敵視和鎮壓。
@@“忠孝之道”與詩人高村光太郎
高村光太郎(1883-1956年),是日本著名的詩人、雕刻家。在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曾赴美國、法國留學,是日本口語自由詩的完成者。作為一個詩風貫穿著理想主義色彩的詩人,堪稱是徹底確立了自我的近代個人。但就是這個詩人卻寫下了打量謳歌戰爭的詩篇,參加了大政翼贊會,並成了文學報國會的骨幹。戰後,他在《愚昧小傳》中用苦澀的語言寫道:“天皇危殆。僅此一語,就決定了我的一切。我看見那裡有兒時的祖父、父親和母親。少年時家中的雲霧籠罩著整個房間。我的耳畔充滿了祖先喘息的聲音:陛下、陛下正深陷危殆——這念頭讓我頭暈目眩。如今只有捨身去保護陛下。”顯然,與河野廣中一樣,“忠孝之道”對於他來說,就像是戴在頭上的緊箍咒。
高村光太郎早年留學法國,在歐洲認識了自由與自我的價值,堪稱得到了靈魂的解放,從而不能不“對日本的事物和國情一律加以否定”。但只要日本是一個家族國家,那麼,對日本國的否定就意味著是對父母的不孝。“母親在我的枕邊小聲呢喃。我該如何處置這樣的恩典和愛情?”顯然,家族國家的“忠孝一致”徹底窒息了詩人的近代自我。
高村光太郎在青春時代曾對“忠”進行反叛,“否定了日本的一切事物和國情”。但按照家族國家的倫理來進行推理,這意味著是對父母的不孝。而他在本質上又不可能成為一個不孝之人。在此,“義在君臣、情在父子”的邏輯就像緊箍咒一樣,讓他不可能去抗拒父親般的天皇。其結果是,無論否定,還是肯定,都得保持忠孝的一致性。於是,高村光太郎在否定和肯定的兩極之間左右搖擺,最終為“忠孝”殉道,積極投身於戰爭之中,為戰爭搖旗吶喊。戰後,為了懲罰自己的“愚昧”,他在岩手的深山中度過了7年孤獨的流放生活。
而高村光太郎不過是家族國家意識形態扼殺了日本近代個人的無數事例之一。
@@家族國家中的個人形像
明治20年代確立的天皇制家族國家體制把“家庭”作為末端組織,將整個社會關係設定為金字塔形的等級結構,並把天皇作為家長置於金字塔的頂端。家族國家掌握著絕對的價值,不允許有其他獨立的精神領域和秩序存在。因此,要想在這樣的社會生存下去,個人就不能違逆某種固定的模式。而這個固定的模式就是適合於天皇制家族國家秩序的個人角色。
高杉一郎的《在極光的陰影下》描寫的是他在蘇聯西伯利亞的被俘體驗記,記錄了在被俘這一極限狀況下,日本人會暴露出怎樣的家族主義式的個人形像。
戰前的日本人是在把國家視作家庭的家族國家裡接受教育,並長大成人的,但戰敗使那種固有的秩序遭到了瓦解。面對一個喪失了秩序的世界,人們感到束手無策,只求明哲保身,變成了徹底的利己主義者,表現為趨炎附勢,追隨大流。俘虜營就儼然是日本軍隊的翻版,在這裡,聲高氣壯就意味著是強者。
當面對等級秩序低於自己的人,他們是那麼趾高氣揚,大施淫威。而遇到等級高於自己的人物,就一下子變得唯唯諾諾,俯首帖耳。權威與奴性、傲慢與卑屈,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交集在同一個人的人格裡。
而且,儘管具有家長權的人對家庭成員具有絕對的權威,可一旦面對上一級的家長,比如,本家的家長時,他又必須絕對服從。顯然,在權威的等級制度中,是依靠地位的高低來決定其價值的。處在離最高權威——如果以整個家族國家為例,就是高高在上的天皇——越近的位置上,就能越發增加其權威性。
這樣一來,極端的家族國家主義體制就使人有了雙重人格。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人不是自主性的存在,個人的價值和行動準則是在家族國家的等級序列中確定的。一旦被陡然拋人一個沒有秩序的世界裡,日本人就會失去自治能力,無法找到基準來建立起秩序。
大岡昇平的《俘虜記》描寫的是萊特島上的俘虜營。隨著戰敗,俘虜們迅速地墮落,從中產生了一個所謂的“文身小組”。當大多數俘虜被允許回國,只剩下戰犯嫌疑人留下之後,他們徹底失去了自治能力,完全被動地聽任“文身小組”的暴力統治。
小松真一在《虜人日記》中也描述了近似的境況。作者參加了菲律賓戰役,投降後被拘留在魯遜島的俘虜營裡。與萊特島俘虜營一樣,俘虜們也完全處在部分人的暴力統治下,直到美軍清除了其中的暴力團夥為止。即便如此,在那裡也很難培育出新的民主自治。
日本戰後派小說家野間宏把這樣的世界叫做“真空地帶”。因為在這裡,沒有誰作為自主性的人而存在著。能夠在“真空地帶”裡如魚得水的人,只能是那些所謂的“識時務者”,或是“精明的士兵”,即典型的家族主義式人物。
在這樣的世界裡,要堅持自我,不隨波逐流,乃是至為困難的事情。在極端的家族國家體制或家族主義的秩序中,價值是從最高家族權力者那兒向下貫穿的。下級者不可能有獨立的價值判斷。與權威呈無限上升的態勢相反,價值呈無限下降的趨向。其間沒有自由之人的存在。也沒有責任感與理性的存在。每個人都僅僅是被操縱的偶人。
其實,天皇本身也逃脫不了家族主義人物的命運。或許只有決定宣佈投降這件事,是他唯一一次想要逃脫家族主義人物命運的嘗試吧。正如帝國憲法上諭的詔敕所言(明治22年2月11日):“國家統治之大權,由朕受讓於祖先,傳承給子孫。”可見,天皇的職責就是忠實地捍衛祖宗之意,其間沒有天皇個人自立性存在的餘地。
國家的家長也不過與普通家庭的家長一樣,乃是永恆歷史中的家在現在這個時點上的管理者和代表者,其作為絕對者的權威亦不過是被家族所賦予的權威。這讓我們想起了日本二戰中的首相東條英機。儘管他掌握了空前的權力,但似乎也逃脫不了同樣的邏輯。在昭和17年12月召開的第81次通常議會眾議院戰時行政特例法委員會上,當喜多壯一郎議員針對首相的指揮權,詢問是否可以認為是一種獨裁時,東條英機申辯道:“儘管常常被人稱之為獨裁政治,但我想首先明確一點:(中略)姓東條之人,不啻一介草莽之臣,與您毫無二致。只是被賦予了總理大臣之職務而已。僅此不同。這也是因蒙受了陛下之光才始得發亮的。倘若沒有陛下之光,我就無異於一塊石礫。敝人是因為有陛下的信任,站在這一位置之上,方能閃閃發亮的。這正是與被稱之為獨裁者的歐洲諸公迥然不同之處。”
對此,丸山真男在《超國家主義的論理與心理》一文中尖銳地指出:“在此表現出因與終極權威的親近性而帶來的洋洋自得的優越意識,與此同時,也袒露了一個頭頂上感受到權威精神重壓的臣下那種小心翼翼的心境。”
的確,一個像月亮那樣因太陽的照射才發光的人,是不會產生責任感的。就連東條英機這樣的最高權力者也自稱是被所謂的時代氛圍所驅使,才隨波逐流地步人戰爭的。顯然,追隨時代的氛圍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以至於在日本,很多時候無個性作為一種完美的人格受到人們的尊敬。在這樣的精神風土中,獨具一格的人被視為異端,而對自由的要求則被視為叛逆。這也意味著,原本作為自由之人的常識,在天皇制家族國家裡竟然變成了危險的思想。怪不得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在《侏儒的話》中不無苦澀地寫道:“所謂的危險思想,其實就是試圖將常識付諸實施的思想。”
@@日本的“家元”制度與近代化
明治以後,日本以驚人的速度實現了近代化,但很快又經歷了太平洋戰爭的慘烈敗北。可二戰之後,日本很快又像一隻不死鳥一般重振翅膀,經過幾十年的時間,迅速成長為世界的第二經濟大國。這其中到底有著怎樣的秘密?美籍華裔心理人類學者許烺光在《比較文明社會論》(培風館,1971年版)一書中,從日本的家族制度出發,探討了這一秘密。他詳細剖析了日本社會的組織原則,從親屬制度和人的心理需求人手,對“家元(iemo-to)”這一日本社會特有的組織模式進行了深人的研究,並結合中、印、美社會的相關材料做了生動而細緻的比較。他在比較日本、美國、舊中國和印度的文明時,始終聚焦在各自的家庭結構及其連帶原理上。既然家庭是人類最基本的社會單位,那麼,人的行動和心理就必然受到家庭內部機制的制約,因此社會結構、社會心理和社會行動的基本模式都不啻家庭結構和關係的投影。他認為,親屬關係是社會成員成長的首要空間,也是影響其待人接物態度的最直接源泉。而處在親屬關係與整個民族及國家之間的二次性集團(secondary group)對整個社會的型塑起著最關鍵的作用。因此,考察親屬關係與二次性集團之間的關係,乃是理解一個社會的面貌的有效途徑。在許烺光看來,日本的家元作為介於親屬關係與國家之間的二次性集團,和中國的宗族、印度的種姓、美國的俱樂部一樣,是日本社會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組織,其組織原則更是決定了整個日本社會的結構。
一說到家元制度,我們腦子裡馬上會浮現出花道和茶道的家元。家元是指在茶道和花道等傳統技藝之道中傳授本流派正統技藝的掌門人或宗家。所謂的“家元制度”,是指家元的繼承者由血緣者或養子這樣的模擬血緣者來擔任,並以家元作為頂點,中間層是向家元申請授藝執照的師傅或已經取得藝名的弟子。而在這些人下面,又集結著打量還沒有被授名的一般弟子。一名弟子在技成後通過鑒定儀式成為家元的正式成員,並可得到師傅的賜名,掛牌營業或開帳授徒以獲取收人。各個弟子之間通過師傅互相聯繫,互相幫助,各家之間有自己的地盤,但不可爭鬥,也不可隨便改投另一師兄弟的門下。大家元具有最大的權威,有權利制定一派的規範,獲得門徒的供奉,其地位可傳與子孫、女婿、遺孀或門中有力之人,只要供奉家元的祖先即可。而所有的集團成員都是根據自由意志,在簽訂契約的基礎上加人進來的,就像一個大型的同族企業。如果一個流派人數過於眾多,就會形成分派,有可能圍繞著繼承權展開內部鬥爭。為了防止這種現像,本家就會積極而自發地派生出諸多分家,在本、分家之間確立縱向的秩序關係,在維持小組織穩定性的同時,又從整體上保持大組織的有利性。
這樣的家元制度之所以產生在日本,顯然與日本傳統的“家”制度密切相關。在許烺光看來,日本的家庭連帶原理是一種緣約原理。所謂緣約原理,就是血緣原理和契約原理的混合體。在這一點上,與中國的血緣原理和美國的契約原理相比,表現出更加複雜的性質。
所謂的血緣原理,就是將血緣絕對化,對非血緣者不予信賴,不將其納人組織內部的原理。即是說,不會讓非血緣者作為養子來繼承家業,即使是妻子,也對其介人家庭設置了一定的限制。
契約原理則將獨立的個人自由意志加以絕對化,把家庭看做是在根據獨立的個人自由意志簽訂明確契約的基礎上人為地建立起來的組織。換言之,是在絕對平等的男女之間締結夫妻契約,以此為基礎來建立家庭。
與上述兩者不同,我們從面前列舉的京都老鋪的事例中就可以明白,日本的緣約原理儘管也重視血緣原理,但另一方面也導人了契約原理。為了家族的永續和發展,即便是血緣相連的嫡子,如果沒有出息,缺乏能力,也可以將其廢黜,或是斷絕關係,而將沒有血緣關係但卻有才能的他人收為養子,以繼承家業。而且,家長達到一定年齡,就會引退,將家長權轉讓給嗣子。顯然,日本的“家(ie)”是以家產、家號而非血緣為延續紐帶的。從上述舉措中不難看出日本式家庭自血緣紐帶向制度性團體展開的趨勢。
如前所述,除了可以收養女婿甚至幼弟之外,日本人的“家(ie)”奉行的是單子繼承製(unigeniture ),因此對家庭中的非嗣子來說,長大後分家另過幾乎是必然的結局。與英美不同的是,分離出去的非嗣子們很難自由地另謀生路,毋寧說為父親選定的繼承人(大多是長男)及本家服務,從而形成本家和分家的關係,乃是普遍的情形。因此日本的有效親屬關係僅限於核心家庭,同戶成員比遠親更為重要,沒有中國那種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和中國一樣,日本家庭關係的主軸是父子關係,但此外還必須加上母子關係這一次軸。由本家和分家再加上地緣因素所構成的親屬體系就形成了日本最典型的親屬組織,即所謂的“同族”(dozoku ),但它不像中國的宗族那樣,僅僅是作為父系的擴大家族而存在。同族不是以個人作為構成單位,而是以制度化的“家(ie)”作為構成單位而形成的一個體系,有著本家與分家之別,而作為統治者的本家很可能擁有多個從屬於它的分家;同一地域的人可以申請加人,無需具備血緣關係;本家與分家之間有等級高低,在禮儀、社會、經濟上形成了較為固定的序列等級關係;儘管以真正的血緣關係為基礎,但又可以包含傭人、佃農等禮儀上的(模擬)血緣者;作為同族構成單位的各個團體分別實施自治,但又在本家和分家之間存在著一種恆久的恩義(債務)觀念。排除地緣因素之外,同族已經具備了家元的大多數組織原則。不過,家元制度是在江戶中期以後,針對町人社會學習技藝而形成的一種制度,大都出現在城市裡,因此不必像同族那樣依賴於地緣因素,從而能夠在規模上得到極大的擴張。不妨認為,家元是把日本親屬關係原則發展到二次性集團中的產物。
由於日本採納的是單子繼承製,家產不均分,全部傳給一個兒子,所以,非嗣子們在原來的親屬集團裡沒有足夠的地位。他們只好要麼給嗣子打工,要麼離開親屬集團,離開農村,到城市去謀求新的職業。許烺光認為,“人”是一個心理和社會的平衡體,稱之為“心理一社會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簡稱PSH)。該平衡體由內向外分為八個同心圓,依次為:無意識、前意識、不可表意識、可表意識、親密的社會與文化、運作的社會與文化、較大的社會與文化、外部世界。人絕不可能作為一個單獨的個體而生活,作為社會成員,必然希望與其他個人保持一種親密狀態。所以,當日本的非嗣子離開親屬集團來到陌生的生活空間,也必然追求那種社會和心理的平衡狀態。但他們的內心還遠不具備那種重視依靠自我的個人主義價值觀,所以,他們要麼把那些組織改造成家庭式的,或者同族式的組織,以獲取在家族集團中才能獲得的親密感,要麼就不得不加人某種業已存在的家族主義式的秩序中,試圖將自己新的生活場所設定在同族式的團體,抑或類似親屬的二次性集團中。換言之,傾向於把家族式的——特別是日本“家(ie)”制度的因素帶人二次性集團中,通過模擬血緣者之間而謀求情愛上的結合,並在自己所屬的組織中去發現“親密的社會和文化”。即是說,作為對父子關係的模擬,誕生了“親分和子分(義父和義子)”的關係,或是“前輩和後輩”的關係。而職位上的上級和下級等,也是通過這樣的關係來相互謀求親密感的。正如面前所述,日本的家庭與西歐相比,有著一個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在家族關係中,西歐更重視契約式的夫妻關係,而日本和中國一樣,更看重宿命式的父子關係。但與中國不同,父子關係這一親屬關係的主軸總是以母親作為媒介的,母親就像大地一樣包容了一切,母子在情緒上具有非常強烈的連帶感,僅次於父子那種制度上的結合,並由此產生了被土居健郎稱之為“甘(amae)”的世界。所謂的“甘(amae)”,原本是指嬰兒擺脫了母子未分化狀態,依舊尋求母親的庇護,單方面地依賴母親的一種心理(詳細論述參見第六章)。當非嗣子們進人一個新的集團時,作為母子關係主要屬性的“甘(依賴)”心理就很可能被帶人上述的集團裡,從而導致成員們對領導人的順從和對組織的忠誠。在日本的社會集團中,母子關係的這種模式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以至於社會集團中的上下級關係也成了它的翻版形式,尋求的是一種情緒上的安定感和一體感。
因此,不難設想,日本的非嗣子們所希望加人(或設立)的模擬親屬組織也必然具有與“家”或同族相近似的等級結構。而在組織的領袖和下屬的成員們之間,也自然會建立一種貫穿著恩義、獻身、依賴的關係。而許烺光把這種貫穿著日本親屬組織原則的二次性集團叫做“家元(iemoto)”它是指以日本傳統藝能中的所謂家元制度為模型的組織形態。
家元制度具有如下的結構特質:一是在具有絕對統治權的師傅(家元)和被授予藝名的弟子之間,存在著庇護與獻身的相互職責;二是在組織結構上,從宗家的家元到末端的弟子之間劃分為好幾個階層,整體上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具有連鎖性的等級序列;三是家元作為流派的最高權威君臨於所有人之上;四是整個組織乃是一種模擬家族制度。對於家元這個組織體的永續來說,上述那種家族式或者同族式的結構發揮了很大的功效。因為把非血緣者的弟子編人模擬家族中,能夠促成他們對組織的自發性忠誠和相互間的和睦,營造一種家族式的溫情氛圍。
顯然,家元是以親屬體系(“家”、同族)為模型所形成的、具有連鎖性的等級制組織。這種組織結構一旦固定化,就會和它所仿效的親屬模型一樣,其內部的等級關係呈現出一種恆久化的趨勢;另一方面,由於家元帶有自由結社的契約式特徵,所以,個人的加人與脫離都伴隨著當事人的選擇意志。即是說,家元的結構原理乃是親屬原理與契約原理折衷後的“緣約原理”。所謂緣約原理,既意味著固定不變的等級制度,同時,又是在一個團體的人們中間自發締結的制度,他們在共同的意識形態下,為共同的目標,一起服從某些共同的行動準則。
所以,儘管在加人家元時成員有自由選擇的意志,可一旦變成了其中的成員,就會自發性地宣誓效忠所屬的組織。因為家元的核心結構就在於那種相互依賴的師徒關係。這裡所說的師徒關係,是指家元中具有連鎖性的、處於等級制中的各個鏈條,其每個鏈條上的關係都具有相互依賴的特點。所謂相互依賴,是指在行動上的價值取向的一種形態。既然每個人都與其他人相互依賴,那麼,就有責任和義務回報從別人那裡所蒙受的恩義。這樣的價值觀普遍存在於家元中,所以,成員們自然容易形成這樣的傾向:把上司看做是最高權威的具現者,從而通過對上司表現忠誠和進行獻身,來實現對整個組織的忠誠。
這種家元制度是在江戶中期以後,針對町人社會學習技藝而形成的一種制度。家元與弟子之間的關係儘管很容易被類比為封建的主僕關係,但事實上,弟子們是根據契約集結到師傅門下的,取得技能執照乃是他們進人師門的目的,而這種執照最終是用金錢來買賣的。顯然,這裡存在著一種近代的契約關係和市場關係,具有同樣適用於明治以後資本主義制度的性質,所以,在被稱之為明治絕對主義政權的天皇中心政權下,得到了更大範圍的發展。
這種家元制度具有廣泛的意義,甚至可以稱之為整個日本社會的組織模式。許烺光在分析了日本的宗教組織和經濟組織之後,認為在這些表面上現代化的組織背後,其內部核心的組織原則和人際關係模式仍舊沒有改變。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的企業組織不啻一種家元制度,而學界、宗教界以及政界都可以作如是觀。總之,日本的組織和集團不管大大小小,無不貫穿著家元的組織原理,即緣約原理。事實上,明治以後的天皇制家族國家就是家元制度的一種具體而又宏觀的社會體現。換言之,有了緣約原理,天皇制家族國家才得以成立,而在此基礎上才有了日本的近代。儘管這樣的近代化帶著明顯的局限性,也引發了種種批判和爭議,甚至一度給日本人和鄰國都帶來了莫大的災難,但天皇制家族國家體制的確是建立在緣約原理上,並沿著這一方向來達成近代化的。
作為日本社會最基本的組織形式,家元既不像中國那樣,是作為家族自身的直接擴張而形成的,也不像美國那樣,完全由獨立的個人在自由平等的立場上締結契約,從而形成自由結社。換言之,日本人沒有廢棄比中國更富有彈性的親屬體系,而是把那種親族結構運用在髮端於西洋社會結構的近代組織中,並利用緣約原理強化其內容。其結果是,在產業、軍事、教育、政治等領域快速實現了近代化。這一近代化的過程卓有成效地利用了固有的親屬體系,與根據契約來實現組織化的西歐模式大相徑庭。與舊中國相比,日本人比較容易從原始的血緣羈絆中解放出來,從而也就比較容易加人到經濟、政治、軍事、宗教、藝術等領域的集團裡。家元作為那種集團的原型,是由眾多具備自律性的下位部分呈等級序列組成的協作團體,作為一個集團,它充分滿足了達成近代化的前提條件,即可以根據選擇意志,在必要時導人新鮮血液。而家元的緣約原理又不同於西方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提供了成員對組織的絕對忠誠、獻身精神等對於近代企業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源。所以,以許烺光為代表的不少學者試圖從日本家元制度的結構和機能中去尋找日本近代化的原動力,認為正是家元這一介於“家”和國家之間的二次性集團及其制度使得日本實現了今日的經濟奇蹟。
顯然,在強調日本社會集團結構的等級序列、同族性質和家族式情感因素等方面,許烺光的理論與中根千枝的縱向社會理論不乏一脈相通的地方,甚至不妨看做是相互補充的理論。
@@家元制度的負面作用
盡管家元制度給日本社會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帶來很多弊端。只要調查一下就會發現,日本大約百分之九十五的公司都是同族公司。並且,一流公司大都屬於同族公司。與此同時,最糟糕的公司也有不少屬於同族公司。就日本式經營而言,同族公司或許是最適合日本風土的公司模式,但同族公司的本質卻又是一把雙刃劍。如果經營者是一個人格優秀的人,那麼,公司的凝聚力就會不斷壯大,讓全體人員在非常時刻能抱成一團,迅速做出決斷,抓住每一個機會。可是,如果經營者把公司視為囊中私物,那麼,公司就會分裂成諸多派系,領導就有可能偏聽,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
在這裡我們可以舉出安宅產業破產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安宅產業的崩潰就是源於同族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人際關係,而由此帶來了公司中樞管理機能的混亂,導致徇私舞弊的打量發生。而這與“安宅家族”的存在密切相關。所謂“安宅家族”是指由安宅會長與其擔任專務的長子擔綱形成的一個集團。從董事到普通社員,據說多達200人。從昭和40年代初期開始,被安宅僱傭的大學畢業生,有一成人左右都會被召集到福井縣高濱的保養所,接受人社前的培訓。會長也會大駕光臨,傾情演講。據說這就是安宅家族的編人儀式。
安宅家族的創始人總是離不開這樣的口頭禪:“安宅是我的,而我的也全部是安宅的。”這裡顯示出一種公私一體化的邏輯。在創始人的時代,同族公司的長處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揮,而進人第三代,這種家族體制就轉化為一種弊端,使公私不分的情況達到極限。以至於專務的交際費每月高達1000萬日元,除了早餐自理之外,一切餐飲費用均向公司報銷。
這個安宅家族的結構就是上述那種家元社會的結構。安宅產業的崩潰暴露了家元制度的弊端。而天皇制家族國家無疑是在最大規模上體現了這種結構的特點。天皇制家族國家是在明治以後,隨著日本近代化的過程而確立的體制,在第一代掌門人那兒,這種體制的長處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揮,而在第三代時就轉化為弊端,徹底崩潰了。因為這種家族國家披上了家族主義的溫情外衣,再加上大力推行忠字當頭、忠孝一致的意識形態,從而具備了非同一般的蠱惑性,以至於當整個國家滑人軍國主義的泥沼時,那種家族主義的凝聚力反而帶來了更大的破壞性,給日本人和近鄰諸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儘管在西歐和中國,也與日本一樣存在著家族制度,但無論是在西歐,還是在中國,都沒有出現家族國家。或許其中的緣由非常複雜,一言難盡,但不可否認,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不承認作為日本“家(ie)”制度特點之一的所謂模擬血緣。儘管都說日本人尊重血緣,但這種血緣並非生物學上的血緣,而是社會血緣。血緣就這樣被虛擬,並被無限地擴大,以至於家族演變成了整個日本社會的結構模式。
如今,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已經崩潰,取而代之的是核家族。日本傳統家族制度因為包含著被擴大為家族國家的因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視為“萬惡之源”,遭到人們的猛烈抨擊。但我們不能不同時看到,那種對社會血緣的尊重乃是其後構成家元社會的要素,並借助家元制社會的穩定性和合理性,使日本成了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毋庸置疑,家族的文化結構作為日本人的基本文化特性,至今扔在影響著日本的社會結構、社會心理和社會行動的基本模式。
---------------------------------------------------------
家庭是由婚姻、血緣或收養關係所組成的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家庭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是指由共同生活且彼此認同的兩人或兩人以上所構成的單元;廣義的則泛指人類進化的不同階段上的各種家庭利益集團即家族。
家庭觀念的演變
在古羅馬,famulus(家庭)的意思是一個家庭的奴隸,而familia則是指屬於一個人的全體奴隸。羅馬人用familia一詞表示父權支配著妻子、子女和一定數量的奴隸的社會集體。
對家庭含義本質的認識是從近代才開始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爲:「每日都在重新生産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産另外一些人,即繁殖。這就是夫妻之間的關係,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家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頁)。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認爲家庭是「肉體生活同社會機體生活之間的聯係環節」。美國社會學家E.W.伯吉斯(Ernest Burgess)和H.J.洛克(Harvey J.Locke)在《家庭》(1953)一書中提出:「家庭是被婚姻、血緣或收養的紐帶聯係起來身份相互作用和交往,創造一個共同的文化」。中國社會學家孫本文認爲家庭是夫婦子女等親屬所組合的團體。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爲家庭是父母子女形成的團體。根據1989年12月8日,第44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宣布1994年為「國際家庭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時的說法「家庭是社會的細胞」。
by J&J
家庭的功能
家庭的功能之一是養育兒童。這是由於人類的嬰兒很柔弱,更加需要成人的照顧。要求至少要有一個成年人與之建立一個密切的聯繫,作為成年角色的模範。在同一個居住體中,雙親的存在提供了這樣的條件。但是養育兒童並不是家庭存在的唯一原因。從理論上講,成群的孩子可以由成對經過訓練的男女專家來撫養。而目前出現的同性婚姻也對傳統的家庭觀念帶來了衝擊。
家庭的功能之二是贍養老人。
家庭的功能之三是性關係的控制。一個人就是通過家庭獲得對另一個人的性接觸權利的。亂倫禁忌是歷史上所有社會都有的規則,禁止家庭內合法配偶以外的成員之間發生近親性關係。
家庭的功能之四是休閒與娛樂功能。無論在什麼社會中,社會成員的大部分閒暇時間都是在家庭中渡過的。
家庭的功能之五是經濟功能。在古代社會,家庭是最基本的生產單位。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分配、消費和財產繼承的功能。
簡言之,生活中家庭具有「食、衣、住、行、育、樂」的多樣功能。
中國傳統家庭
一個中國傳統家庭通常採用一夫多妻制,且多代同堂。這樣的一個家庭稱為擴大式家庭。[1]
觀念
中國傳統家庭有以下觀念:
父子關係的重要性
父子關係是中國傳統家庭中最重要的關係。世係的家庭錄由父到子,由一代到另一代。孩子亦從父中繼承財產和地位。中國傳統中,女性成員會在結婚後成為丈夫家庭的成員。[1]
夫權家庭
父親是傳統家庭最有勢力的人。年老的男性成員有權力去決定重要家庭事務。其他成員必須服從他們。[1]
多代同堂
在一個理想的中國傳統社會,很多後代和袓先會和諧地居住在一起。[1]
敬仰袓先
一個中國傳統家庭重視敬仰袓先。家庭成員有固定的儀式敬仰袓先,以表示對祖先的敬意。[1]
家庭傳統思想和聲譽的重要
一個中國傳統家庭重視道德教育,因為家庭的不規矩會損害家庭的聲譽。[1]
孝道和長輩的重要
中國傳統家庭為了加強父親,兒子和兄弟的角色,對孝道十分重視。俗語有云:「父慈子孝,兄友弟重」和「百行以孝為先」。
中國傳統家庭亦重視年幼服從,尊重年長的宗旨。[1]
男女之間工作的不同
在一個中國傳統家庭中,男性擔任領導的角色,而女性擔任從屬的角色,他們有不同的責任;女性集中從事家庭事務例如照顧年老和年少男性在家庭外工作,賺錢養家。俗話多說男主外女主內。[1]
---------------------------------------------------------
名·自サ 死得沒價值,白死。
つまらぬことで犬死するな
死的沒有價值;白白地死
不能因為一點小事就白白死掉
森鷗外是日本明治時代的文學大師,曾在歐洲留學,擔任過日本陸軍軍醫總監,創作有《舞姬》、《高懶舟》等打量的文學名著。他於1922年發表的《阿部一族》在日本是一篇膾炙人口的小說,講述的是日本中世紀肥後(即現在的熊本)藩主與阿部家族的對立,譴責了武家社會非人性的一面。事情髮端於寬永18年(公元1641年)肥後藩主細川忠利的病故。當忠利危篤之際,有19名隨從提出殉死的請求,但只有18名得到主人的恩准。在當時,不被恩准的殉死是受到嚴厲禁止的行為,被稱之為“犬死”。不能因為一點小事就白白死掉
可是,在這18名殉死者中間,居然沒有包括在眾人眼裏理應殉死的阿部彌一右衛門。他自幼便跟隨在主君身邊,而今已是俸祿超過千石的武家,可主君卻沒有賜予他殉死的機會。據說是因為近來主僕之間出現了齟齡的緣故。於是,不斷有風言風語傳人阿部彌一右衛門的耳朵。最終他為了證明自己絕非卑怯之人,不得不在未獲主君恩准的情況下剖腹自殺,為主君殉死,以洗刷自己的污名。在中世,殉死者的家業將由後嗣全部繼承,並得到主君家的格外厚待。但阿部彌一右衛門的遺族們卻受到了不公平的冷遇。他的嫡子權兵衛沒能繼承父親的家業,其1500石的俸祿被分別給予了阿部彌一右衛門的弟弟們。儘管合計起來,俸祿的額度與以前相同,但阿部彌一右衛門的本家卻走向了衰落,遭到眾人的白眼。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