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社會裡佛教、道教分野模糊,但皆主張因果論,小時候常看到、聽到因果報應的故事,深受因果輪迴的薰陶。前世因果對凡夫俗子的我輩來說太過玄妙,然現世因果卻是淺顯易懂而容易忽略的道理,值得我們探討警惕。
俗話說『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其實因果是相互循環的,『塞翁得馬、塞翁失馬』的故事道盡了其中趣味。聽故事歸聽故事,現時生活中因循苟且,以致不能自拔的困境才是我們需要理清的頭緒,譬如說人們習慣晚睡,必定不能早起,所以晚睡是因、晚起是果;但是晚起也造成生活步調延後,勢必再度晚睡,此時換成晚起是因、晚睡是果,因果相互循環下已分不清因果關係了。
因為因果是相互循環的,常導致因果錯亂,導因為果、導果為因,結果變成捨本逐末,找不到治病的根源。譬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如果頭痛、腳痛的背後還藏著其他病灶,就成為典型的治標沒有治本,怎麼能治得好呢!
白話文學大師胡適名言:『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想要享受鮮美的果實,必須先起個因做足功課。前世因果已成定論難以改變,現世因果才是我等需要努力的方向。
試問你我有沒有遭遇過搥首頓足、懊悔不已的時候?痛苦之餘有沒有試著探究原因?有沒有因果錯亂,搞不清楚問題的方向?唯有撥亂反正、對症下藥,才是避免再次懊悔的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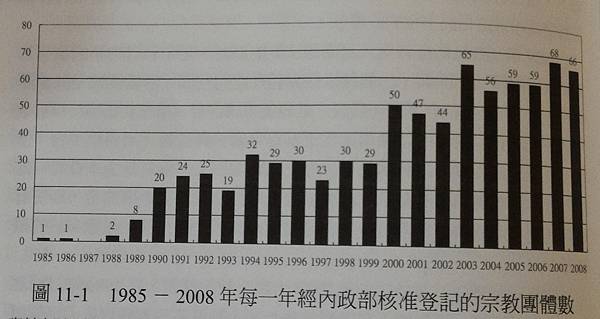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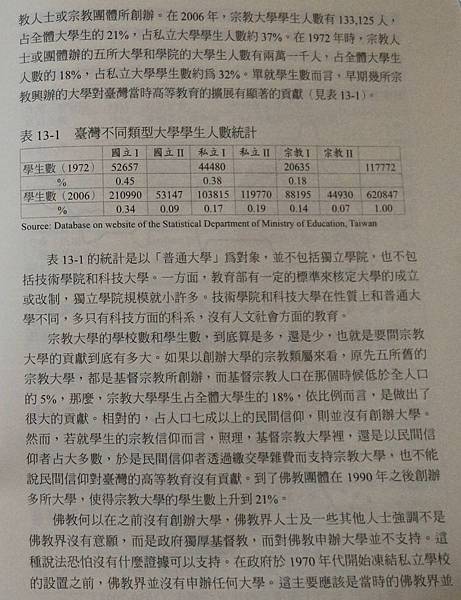




----------------------------------
禪空與上帝
——關於基督教和禪宗的對話
■ 麻天祥
□ 梁燕城
𨪜𨪜無執的本體論
𨪜𨪜□:很長一個時期以來,一直希望有一個基督教文化與佛教文化的對話。在此之前,儒學與佛教,儒學與基督教,以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都有很多對話,並且在國際上舉辦過一系列的討論會,我也參與過。而在基督教與佛教方面,在夏威夷大學曾辦過大型的國際對話,且出版有學刊。但中國在過去較少深入地進行討論。最近幾年,我比較關注從深刻的文化和學術角度來思考佛教問題,然後再看一下基督教文化對這個問題有無回應。這個對話可能填補這方面的空白。當然一般俗世的宗教現象,會有很多滿天神佛的拜偶像迷信,涉及虛假妄識,這是另一課題,如今且放下不談。回到原初的哲學智慧,我想可以從禪宗討論起。因禪宗佛學較多哲學智能,較少迷信妄習。首先,針對「空」這個概念,大概印度的龍樹強調空,作為佛學的核心思想和經驗,而這個空的哲學與中國佛學後來空的概念並不一樣,龍樹是完全從緣起提出性空,基本上是不講本體的,空只是緣起生減所呈現的一種空性,即指萬有沒有不變的本質,空是不能用任何範疇來定義的,是不一又不二、不來又不去、不生也不滅之類的,龍樹是通過破掉各種知識範疇而建立空的緣起理論。但是,空的這個概念到了禪宗,它的發展是很有意思的。禪宗的開宗大師應該是達摩大師,用的經典還不是空宗的經典,是用《愣伽經》,是屬於印度的「如來藏傳統」,比較講本體的,是屬「有宗」的傳統。到了六祖的時候,禪宗才轉向空,但這個空已經跟龍樹的空不一樣,六祖的時候,神秀是「有宗」的觀點,所謂「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是一種有本體的觀點,但是六祖「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這個說法已經是「空宗」觀點,否定有不變本體,這也開出禪宗很重要的發展。對禪宗來說,空的概念與龍樹的空又有不同,因禪宗又講「見性成佛」,此中的「性」是否本體呢?這個問題很有趣,因為一講佛性還是離不開本體,見性成佛還是跟本體論認識有關係的。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本體論呢?我用英文說是一種no committment ontology,理論上不投入任何觀點與範疇的本體論。在龍樹是破一切本體論,但到禪宗、六祖不是以緣起講佛學,卻以中國佛學所強調的佛性來講,故原則上是有本體論的,然而是沒有投入任何觀點與範疇的本體論。這種沒有本體的本體論,或者無執的本體論,其表現永遠是以「公案」的方法存在,通過很多小故事,在日常生活中脫掉任何本體的認定,因而可以投身去任何世界觀、宇宙觀、本體觀,然後又都把它解脫掉,來瞭解這個本體論。這是我對禪宗的理解。
𨪜𨪜禪宗對空的看法
𨪜𨪜■:梁博士對佛教的理解超出一般人的看法。你談到空的時候,我突然想到老子的一句話,李約瑟和侯外盧都十分重視這句話: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三十根輻條集中在車軸穿過的圓木上,那空的地方才是車輛可行走的有用之處;器皿上有空的部分,才是人們有用的地方,可以放物;窗戶有空的部分,才對人有用,可以取光;也就是說,建造房子必須建造一個空的東西,搞建築學的人,必須認識這一句話。一位建築學家跟我講過,有用的部分恰恰是看似無用的部分,看上去砌牆時磚是很有用的,但人在用的時候恰恰不是這磚牆,而是空的部分,這就是中國人的空的觀念。其實你剛才講的佛教龍樹對空的理解,就是不講本體的。我的意思是,佛教是無本體論,還是一種叫非本體論。他們認為世界上的事物不是如道家所說的道是一,一生二,二生三,源處就是道,他們認為沒有本體,一切事物都是互和而有,此有即彼有,此滅即彼滅,此生即彼生。因為有了光明,才有了黑暗,因為有了前進,才有了後退,有了有,才有無,這一切都是相對的,一切事物都沒有自性,是互相依存的,說它有,沒有自性,因為有個無對著它。所以,一切事物都是空的。空的意義並不是說沒有,而是說空的意義沒有自性,比如說水,是氫和氧合成,沒有氫和氧,就沒有水,所以水沒有它的自性,水是空的。但是,我還有一個看法,這個空人們對它解釋不通,有人說,佛教是空的哲學,空的哲學就是虛無主義哲學。其實,佛教是相對主義的哲學,但是這一點似乎還不夠,範文瀾就說,佛教是怕死的哲學,道教是貪生的哲學。說道教是貪生的哲學還有一點理由,但說佛教是怕死哲學就講不過去了,因為佛教追求的境界是永生,是超越生死的,生和死是對立的,生沒有自性,死也沒有自性,追求的是不生不死。胡適有一個看法,印度的禪宗(或佛學)是一種定的哲學,而中國的禪宗佛學是一種慧的哲學。他舉了一個例子,古代印度要找一個大臣,看誰的性命、立命最厲害,就可以當大臣,然後揣一砵油,從城東走到城西,如果灑一滴油就要砍頭,這個人就揣了一砵油出來,從城東走到城西,路上有馬蜂蟄他,有美女從身邊經過,都是動心的,他就堅持下去,想到自己反正是要砍頭,就這樣平揣著從城東走到城西,胡適說這就是印度的佛學。而中國的佛學則是另一個故事:講一個老賊和一個小賊,老賊因為年齡大要退休,為了讓小賊學到手藝生存下去,就讓小賊跟著自己出去偷東西。老賊把小賊領到一個財主家著,並沒有偷東西,而把他反鎖在櫃中,然後出門大喊有賊,家丁趕來,並沒有發現小賊,但小賊在著面也出不去,心生一計,在櫃著學老鼠叫,家丁一聽忙把櫃打開,小賊拔腿就跑,被家丁追到河邊,無路可跑,脫下衣服,包著石頭,扔到河著,往旁邊一躲,保著了一條命。小賊回去找到老賊,抱怨他把自己扔下,老賊問了他如何回來的,然後說,行了,你的手藝已經學到了。這就是沒有辦法中想出的辦法。所以,中國佛學、禪宗就是慧的哲學,這是胡適的看法。
𨪜𨪜否定的智能
𨪜𨪜當然,有的非常有道理,有的(如範文瀾)就沒有道理。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為空在某種意義上是否定。佛教有一句話「空其所空」,不僅要否定現實,否定有,空是對有的否定,同時也是對自身的否定,即空其所空,否定之否定。我基本上界定佛學的哲學是雙向的二重否定。所謂雙向,就是兩個方面的否定,一個是否定萬性、外界的存在,客觀世界的否定,二是否定內性,人無法我,無法無我,就是諸行無常,事實上既否定了內在世界,也否定了外在世界,就是剛才你講的不一不二,不生不滅,一切都是超越兩者之間的空。是一種否定的哲學,否定現實世界,承認在彼岸世界還有一個凈土世界,用虛無飄渺的彼岸世界來否定現實世界,用來世否定今世。這種否定形成一種出世的觀念,這肯定不符合人們的要求。因此還有第二個否定,就是否定出世,否定來世,否定彼岸世界,重新回到內心世界。所以我認為佛教基本上是一種否定,不僅否定外,而且否定內,不僅否定現在,而且否定彼岸。佛教表現了一種徹底的否定,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人生皆苦,都是一種否定。佛教傳入中國後,有許多改變,剛才我說的老子的空,這個空與佛教的空還不一樣,但是佛教總是一種否定,而老子的空是要強調自然,人所重視的不是人工的東西,而是自然的東西,不是那些「有用」的東西,恰恰是無用的東西。隋唐以後,佛教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否定外界,否定內心,看上去是有本體了。而原先佛教是無本體的,佛教進入中國必然是有本體,雖然始終不強調本體,但回到內心的時候,強調的就是內心的本體,也就是心本體。這個意思是說,世界的一切根源是從哪著產生的呢?不是從很遙遠的過去,而是從很切近的現在。所以,鈴木大拙講禪宗都把西方人傾倒,他說,禪講的就是以本性為原性,整個以無限遠的半徑畫出的一個大圓。這也就是說,人的心靈可以無限膨脹。但我的看法不一樣,禪宗的思想就是否定,禪宗有一句名言,三十年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三十年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過三十年,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這充分反映了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思想。因為,起初你看山和水,並不知道山是什麼,水是什麼,後來你內心世界昇華後,知道山和水的內容是什麼,就看上去什麼也不是了。當你把握這個本質後,一切又會還其本來面目。這再過三十年與三十年前是絕對不一樣的,有一個質的飛躍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否定。所以胡適說隋唐時期的佛教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次偉大革命,由原來的無本體變為心靈的本體,由原來的外在超越變為內在的超越,但後來又有雙重性,到近代的一味救亡圖存,對原先的內在超越外在超越進行否定,高度形成了一種參與精神,也就是入世精神,這個不多說了。
𨪜𨪜禪宗在中國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就是充分把握了否定。剛才你說的菩提達摩的禪宗是從印度傳來的,以《楞枷經》為基本的經典,然後到慧能的時候,主要就是《金鋼經》,也就是說,中國禪宗的建立,是《金鋼經》對《楞枷經》的革命,這是胡適的觀點。我認為胡適的研究有啟發意義,實際上就是一種內在的超越對外在超越的改革,也是一個內在化過程,當然也是一種超越精神。我所說的六代禪宗,從菩提達摩一直到六祖,基本上都是假的,大家都是傳說,相繼成習,都認為是真的。其實我認為恰恰不是真的,而慧能的《六祖壇經》是真實的。禪宗是什麼?就是壇經,壇經充分反映了禪宗思想。這個思想我認為有兩點,一是否定,二是超二元對立的思想,我們一般人思維方法就是二元對立,不是好,就是壤,不是有,就是無,不是生,就是死,永遠也擺脫不了這二元對立的模式。可是在禪宗看來,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二元對立的,都是超二元對立的。所以,人們語言一表達的時候,就是「有」或「無」,問題在於語言表達有限,只要用語言、文字來表達,就不能反映本質。我認為超二元對立思想的現實意義很重要,人總是希望對立的東西,讓世界亂一亂。
𨪜𨪜毛澤東曾問趙朴初,此名趙朴初,非是趙朴初,是不是佛教思想?趙朴初答是;又問,是不是先肯定,後否定?趙朴初答:不,是同時肯定,又同時否定。我認為趙朴初的思想很對。這就是佛教的思想,同時肯定,同時否定。但我們人往往不是這樣,掙錢的時候拼命掙錢,掙不到的時候就自殺,得者喜,失者悲。現實生活中特別需要有超越精神。現在中國大陸,評職稱一評就評出人命。禪宗有一個故事,有人半夜起來,一腳踏了一個東西,哇哇大叫,一夜睡不好,第二天醒來一看,是踩了一個茄子。所以,一定要破心著那個執著。禪宗還有一個故事,有一個老太太,兩個女兒,一個賣傘,一個賣鞋,天天哭,下雨了鞋賣不出去,不下雨傘又賣不出去,一個禪師告訴她,下雨了傘就能賣出,不下雨鞋子就能賣出。所以說,這個思維方式要改變,禪宗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禪宗還有一層意思,放下即是,隨順本性,隨順自然,日日是好日子。人之所以弄不好,就是放不下。以上講的兩點,基本上就是禪宗的思想,也基本上就是老莊的思想,是披著袈裟的老莊哲學,而且是大眾化的老莊哲學,如後來中國文化受到禪宗影響,王陽明說,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一直鬥,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革悟。他講無善無噁心之體,就是要超越善和惡之間的對立,他說的善是不是絕對的善,或與惡不對等的善?鈴木大拙說,要超越肯定和否定之上的那個絕對的肯定,那個超越絕對的肯定還是肯定,還是不行,而是應該超越那個肯定與否定之上的那一層另外的否定。有人說,中國的禪宗受了老莊影響,誰都同意,但說中國禪宗是大眾化的老莊,恐怕有爭議,但我認為這是一個事實。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重組了中國的人生哲學,相對儒家思想來說,佛家非常現實,認為現實社會非常不完美,具有一種批判精神,「空」就是否定,運用到社會中,就是一種社會批判意識。我說禪宗是披著袈裟的老莊哲學,或是大眾化的老莊哲學,禪宗講的三十六對,一定要超越那三十六對,後來禪宗搞得愈來愈複雜,就走入邪路了。所以,研究真正的佛學、禪宗,不能到寺院著搞,研究基督教也不能單到教會著,因為那些地方都變成外在的形式,不代表天國,基督教在馬丁路德的改革以後,真正的天國是在每個基督徒的心著。
𨪜𨪜無形像的上帝可破一切執
𨪜𨪜□:事實上,就佛教的思維方法來說,我也認為是一種辯證法,不過是一種「反面的辯證法」,不是綜合的辯證法。馬克思認為,包括黑格爾在內的西方辯證法都是最後走向綜合的,而佛教龍樹的辯證法則是相消的,兩邊都沒有真諦,是相消之後形成的一個中道,而這個中道也是很說不清楚的。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相交並被吸收,重點是在中國哲學的人性論框架下將佛教吸收進來,佛教也變成以心性為本的一種本體論的佛教,但這種本體論也不是儒家的本體論,而是一種破掉一切,講不出什麼內容的一種本體論,也就是天臺宗所提出的不可思議境界。不可思議這個詞很有意思,佛教指語言和思維都不可能及的境界,《維摩詰所說經》說「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而慧遠《維摩詰所說經義記》說「不思據心,不議據口,解脫真德,妙出情妄,心言不及,是故名為不可思議」。另外,「無住」這個詞,六祖的禪宗很重視金剛經所論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維摩詰經特別講過「從無住立一切法」,一切法都是無住為本,這都是在本體論上說不清楚的,也是非常吊詭的,這是破或否定一切自性的觀念。在西方基督教傳統著,有沒有這種破執和不可思議觀呢?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因為從表面上看來,西方基督教受到希臘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影響,重視實體哲學,其神學系統把上帝看成一個實體,變成一個實有的形而上學,不是佛教那種空的本體論。但是我們如果看聖經本身,它本身也是用亞洲的智慧形態去表達,希臘化以後的基督教才成為西方的形態。原本聖經的觀念很有意思,也講到空的觀念,如《新約.以弗所書》講到耶穌基督的「虛己」,在原文是指空化了自己,意即空化了他自己作為上帝的身份才降卑成為人,甚至是奴僕的樣式,上帝代表了偉大光明的真理,但聖經說耶穌成為人的僕人,變成受苦的人,也就是把人以為上帝的光明相去掉,這就有破執的空的意味在著面。也就是說,人從概念上想到上帝的某些樣子,或偉大本質,很易成為一種偶像將無形象的上帝偶像化,而上帝卻將這些人設想的樣子全破掉。你以為上帝像個白須公坐在天上,不料舊約聖經中的上帝卻指明不能用任何形像相狀或偶像形式來表達他。你以為上帝來到人間是多麼偉大、隆重,結果他道成肉身,顯示一個最平凡的樣子給你看,跟普通人一樣,是一位木匠,一個從平凡中透露不平凡的主,最後受盡各種痛苦而死,降到最卑,然後才升到最高,死而復活。這是聖經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𨪜𨪜上帝的隱藏性
𨪜𨪜另外,馬丁路德提到一個特別觀念,即義人同時又是罪人,這是甚具吊詭智慧的。人是一個完全的罪人,又是一個完全的義人。德國的辯證法就是從馬丁路德精神影響出來的。而且他也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上帝不是以他的光榮讓我們知道他,卻以釘十字架的受苦形像向人類顯明其愛與寬恕。所以,上帝的啟示仍有隱藏性,真正的上帝是人永遠不知道的,人想像的上帝是「光榮的上帝」,跟耶穌的表現完全不一樣,耶穌的到來就是解脫所有這些人類執著之「光榮」外衣。明白上帝的深度豐盛,是超乎人概念之外。由此,我發現在基督教神學著面也有空的智慧。事實上我們追溯古代舊約聖經的精神,即知上帝是不能用任何偶像來表達,也不用任何人間的觀念或者人間的系統、人間的雕刻表現出來,這大概也是四千年前猶太啟示宗教的一個很大的智慧,當然這是比佛教更早多了。所羅門王在傳道書提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虛空」,萬事都變化無常,是不斷輪轉下去,這個智慧書,比釋迦牟尼還早三百年左右。中東文化的破執與空的智慧觀念,也就是從那個時候形成和發展出來的。整個聖經著對上帝的表達,往往是出人意表,破除人的執著,如猶太人以為上帝會救自己的選民,但在《舊約.耶利米書》中上帝卻批判選民的罪,說明其後果是被外國攻滅,上帝不會拯救。在新約時代,人以為救主很光榮地來人間,但耶穌卻成為一個受苦的僕人來,你以為他如何,他一定會出人意料地與你所想像的不一樣,不斷破除人對上帝的觀念。這顯明了一種自由的空間,來自信仰超越理性的因定思維,才可使心靈得到釋放與自在。基督教很特別,跟後來的自然神學不一樣,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有他自己的自然神學,通過宇宙的奇妙規律和起始原因來推證上帝存在。西方文化就是希臘的理性與猶太人的信仰之微妙結合,產生了西方的基督教文明。
𨪜𨪜此外我也注意到在東方的基督教傳統,如東正教的發展,說上帝必須通過黑暗來瞭解,而不是通過光明來瞭解,這也是一個著名的靈修傳統。在中世紀的初期一位東方教父名叫尼沙的格理哥裏,主張從黑暗去體會上帝,比如摩西攀西乃山,攀到山頂才見到上帝,而高山有很多雲霧包圍著,爬到雲霧著面時,後面的世界就不見了,這代表心靈超越至高境界,須經過黑暗,使世俗繁華與利欲的世界隱退了,經過了雲霧的黑暗,這才發現上帝的靈光閃現,人必須破除人對欲望的執著,才能領會上帝的臨在。但是我也注意到,摩西爬到山頂時,再從山頂下來的時候,還是回到人間。據聖經講他臉上帶著上帝的榮光,把他經驗的上帝神聖光輝帶到人間。這種黑暗的神學,那時也叫否定的神學,格理哥裏提出否定神學,還有一個丟尼修提出「神學是要說明上帝不是什麼,而不是說上帝是什麼」,凡是清楚界定上帝是什麼的,都是用人的概念設計,不是真的上帝。這層意思似乎就跟禪宗的破執和否定進路很接近了。其實東歐和俄羅斯有很深厚的靈修傳統,問題是以後列寧和史達林統治下,這種神學一直沒有得到重視,而西方也沒有重視。到最近十年,因為東歐和俄羅斯發生變革,這些觀點也重新被發現。似乎在西方世界還有另一種東方傳統,類似中國禪宗那種傳統,修道時把執著全部放下。
𨪜𨪜在十四世紀君士坦丁堡還沒有被土耳其攻下來的時候,爭論要不要西方的亞里斯多德和多瑪斯阿奎那理性神學,那時候多瑪斯在西歐影響很大,也有人到東歐去宣傳,從宇宙的因果律來論證上帝的存在。當時有一個聖人叫巴勒馬的格理哥裏出來,認為基督教本來就不是憑理性來信上帝的,而是憑修養來領悟上帝的。結果,後來東歐和俄羅斯就沒有接受多瑪斯的哲學和神學,維持了一種否定神學的傳統,不以任何概念來論定上帝,這也變成一種很自由的精神,很個人的精神,成為俄國文學的泉源。後來馬丁路德多少也發展這種精神,強調上帝不是有代理人的,人不可能代表上帝來說話,完全是個人憑信心跟上帝的關係,個人的尊嚴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發揮出來。基督教的這種轉變,似乎都與禪宗的思維模式有相通的地方。如果基督教把亞里斯多德以來的那種實體的神學拿掉的話,基督教也可以吸收中國文化的觀念,開出一種境界形態的神學,然後也可以接受上帝本是超越一切的本體,故可以有一種自由而不投身在任何一定理論的神學,強調有一種很自由的與上帝交往的崇高的境界。是上帝直接對個人的救贖,也是人直接的靈性與上帝會面。你剛才也提到,真正的佛教不是在寺院,真基督信仰不是在教會,但是,如果你有最高的體會、體驗、領悟,也是可以回到寺院,回到教會,這種自由精神可以回到最具體的宗教禮儀場合,把新的生命帶回來。事實上在宗教中也常常有這種更新的活動,一個年代有一定僵化、教條,又有人出來把真正的生命轉活過來。我認為以空這個觀點,基督教跟佛教在這一點上是可以深入對話的。不過基督信仰並不以緣起之空為宇宙根本,卻以上帝之絕對超越構成無執本體,也以上帝絕對的愛,回到人間。這引發另外一個問題,即:慈悲是什麼?佛教常常講慈悲,佛是個覺悟的人,也產生慈悲心,然而佛學又以空或緣起是宇宙基本的原理,那麼,慈悲應該也是沒有自性的,虛妄的,然而從佛教來說,慈悲大概也不是虛妄,應該也是很真實的。究竟慈悲是有自性還是沒有自性,如果有自性,當從一種愛的本體論出來,如果無自性的話,佛的慈悲就不需要談了,因為它本身可有可無。究竟慈悲是空抑不空呢?這是佛家的一大問題,亦是空的理論與愛的本體能否結合的問題。上帝是一愛的本體,也是慈悲的根源,在聖經中一切空的講法都是破除人的迷執,終歸則如所羅門所言,「總意是叫人敬畏上主」,回到愛的本體。佛教是否能回到慈悲為本呢?
𨪜𨪜基督教與禪宗佛教對話
𨪜𨪜■:談到基督教與禪宗佛教的對話問題,我想到,聖經的翻譯在有一些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原來希伯來文的神靈叫Logos,我們叫「道」,聖經叫上帝,原來中文本的翻譯比較好,有一句是「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這種翻譯簡直妙極了,「道」的觀念在中國就是道家的思想,太初是道,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我認為這道就是自然,就是空,佛教基本是吻合道家思想的,而英語的翻譯,就是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這種道雖然體現了兩種不同文化的價值,但肯定是相通的。胡適曾經說過,禪宗是一種超語言的思維方法,就是一種瘋狂,瘋狂就是一種方法。所以,東西文化,包括基督教和禪宗,更重要的是在根上是一樣的。比如你剛才講的慈悲問題,應該是有自性還是無自性的問題,其實任何一種理論都有自身的矛盾,所謂追求無本體,最終還是有本體,其實慈悲論是從因果論出來的,因為佛教認為,萬事都不是自性,有因有果,有這個因就有這個果,有這個果,就一定有這個因。因果論化在民間的時候,就不管這個理論是什麼,而堅持有善因就有善果,有惡因就有惡果。我認為無論哪種文化,只要它長期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因為它們所追求的東西,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即人類最佳的生存環境。有人說,有學問的人看宗教是迷信,沒學問的人看迷信是宗教,這就是對宗教的理解差異。其實,我認為在宗教問題上,表現了人們對這個世界是無限的一種理解。人類認識是有限的,但人類意識的能力可以膨脹到無限,因此要用有限的能力去解決無限的世界,這就是宗教。從這著還可以探討出來,包括佛教的中國化,禪宗與老莊的相通,還體現出任何的文化在將來或現代,都可以融合,不是完全絕對的衝突。我認為湯用彤研究佛教史就是為了證明,中印文化可以融合,那麼中西文化也可以融合。不能因為政治現實的不同,而排斥文化的共同性。剛才說到禪宗,禪宗的後期強調隨緣,隨身自然,放下其事,這種思想本來是在否定的基礎上,所以後世的很多人都變成了政治和尚,不是在否定的基礎上隨緣,而是把禪宗對現實社會的批判精神完全丟掉了,就只有隨緣,結果把一切的否定變成一切的肯定,這是後世禪宗愈來愈糟糕的一個原因。有人認為中國落後總是中國文化不好,我認為這不是原因,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起作用,但文化畢竟是軟的東西,在某些時候常常受到權力的扭曲,不會按照文化的正常軌道發展。但反過來,文化在某種意義上也往往可以決定權力,會影響到權力,這可能是我們研究的一個結果。文化有時會受到政治甚至經濟的影響,但文化本身還是會按照自己的軌道向前發展。以禪宗佛教來說,起碼在三個方面影響了中國。一是重組了中國人的人生哲學,二是增進了中國人的理性思維,三是塑造了中國人的特殊的審美觀。而這幾點都與基督教有相通之處,因為基督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重組了西方人的人生哲學,塑造了新教的倫理精神,塑造了西方資本主義精神,如神召喚人、救贖論、原罪說等等。這說明無論是西方文化,還是中國文化,都對人類有極大的影響、決定作用。當然,這不否認文化本身受政治、經濟影響,甚至也不能完全避免某些人屈服於政治的現象。這是沒辦法的事情,關鍵還在於馬丁路德最後所講的,基督教是維持信仰便是得救。
𨪜𨪜慈悲本體與上帝恩情
𨪜𨪜□:這個很對,就是馬丁路德的所謂因信稱義,也是很高明的,問題是如何瞭解上帝呢?用中國的觀念來瞭解,剛才提到的慈悲問題,或者中國人的仁義觀念,對認識基督教都很重要。慈悲或仁義都是一種很高的體會,也就是說你突然發現心中流露出一種對他人苦難的關懷的不忍之心,不安之心,這種自然流露大概就是人性本體的呈現,那麼,這個慈悲主動流露的本質在哪著呢?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的本性是從天而來,是宇宙原來本體的表現,或者認為佛性等同慈悲,不只是由業感因果而生,這樣的話,宇宙的本體就是以慈悲為體,不只是緣起之空,空只是體悟慈悲的一種否定方法。從這點上,佛學就可接近基督教信仰了,因為如果慈悲是一種情,慈悲本身是宇宙本體的呈現,那麼宇宙本體自必有情,這是宇宙的一種大愛親情的本體,亦即所謂上帝,這大愛親情的上帝也可以主動跟人類相交。若真有這愛的本體與人接觸的紀錄,就是上帝的啟示。上帝與人建立關係,對人有救贖,是為其「恩情」,人稱這恩情的上帝為天父,上帝就其自身是超越的,超越任何語言和形像,但上帝也創造天地,從虛空中造出物,故萬物生滅變化,本性為「空」,而他也創造出萬有的規律,故一切均有「道」,他更在人性中刻下慈悲美善之「天命」,成為一切人性美善的基礎。當這人性流露時,就是惻隱與慈悲了,成為佛性與天命的體悟。人生體驗中能夠從兩面遇到慈悲的真理,一個是從反省發現人性著面的慈悲,一是當發現人的自我中心,與種種自私醜惡,需要潔淨時,或經驗大悲苦衝擊時,用信心開放自己,碰見了愛自己的主宰,就是上帝主動跟人類相交而產生的一個特別經驗,這就是宗教經驗。是基督教的傳統,影響了西方的傳統。至於中國人的傳統,重視從人的不忍之心發現人性從天而來,遂從內心發現上帝的天命,是一種內在的超越。聖經則比較強調人與上帝相關的層面,而產生的一種親情的感通。西方的希臘哲學,以理性推論因果關係的最終原因,就變成外在超越的上帝了。基督教本來重內心的感通,而不是外在超越,當基督教來到中國時,也可以與中國的內在超越進行對話與會通。
𨪜𨪜道與中印文化的交會
𨪜𨪜另外,有關道家的「道」這個觀念,據說,中文聖經用「太初有道」一句,是嚴複提議的,這是很奇妙的一個翻譯,把Logos的精神表達了出來,而Logos的原文就是有萬物規律的意思。道同時也有語言的意思,與Logos頗相合,中文著的「道」這個字比英文中Word一字跟希臘原文是更為接近的。但道的觀念跟佛教不是完全一樣的,跟龍樹的緣起的空不同。
𨪜𨪜印度看宇宙人生是變化無常,沒有本體論,否定一切就可以,因為一有理論系統,真相就看不到了,但當你破掉一切系統的時候,最終就必是出世間法,佛學始終是出世間為本。智能高的人看透一切,都跑到山林著面去,坐著不動,印度最智能人士都是在山林靜坐冥思,因為宇宙既沒有什麼本體,也不用追求什麼偉大的理想、正義、奮鬥,因為追求什麼總是無常和空。故此佛教傳來中國,不能不吸收中國文化的人性觀,講佛性,也講在生活中悟道,甚至講「人間佛法」、「人間淨土」,均是要克服印度佛教的退隱傾向。在中國哲學來看,同意宇宙是變化,但變化也不是無常,卻是滅以後還是有「生」,不是空,而是創造性的宇宙,「生生」這個觀念就在中國哲學提出來了,所謂生生不息。《易經》強周「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此外,中國道家也提出道的概念,就是一切的變化總是有它的常道,變中有常,常中有變,常道就變來變去總是有一個平衡在中間,或者說和諧點在中間,而且這個常在《易經》就是生生不息的創造性本體,所以人也可以自強不息,這就變成中國的宇宙觀。到了最高境界還是回到人間,與普通人完全一樣,因為最高真理是不離開普通人的。《中庸》講到匹夫匹婦,至誠之道,就在那著開出來的。那麼,這種思想在印度的佛教著面原本是沒有的,而中國把這個精神在禪宗著開了出來。禪宗也是很重要的一個中印文化的綜合。現在西方文化過來了,如何把中西文化綜合起來,也是一個大問題。
𨪜𨪜主動的慈悲真理
𨪜𨪜或許當代中國,面臨歷史上第二次大型的文化變革與融合,也許就在這個年代。第一次是印度佛教帶來的衝擊,第二次則是把西方進來的文化加以吸收。近代對西方文化的吸收都是有偏見的,特別是把基督教排斥掉,認為宗教是迷信,只談科學與民主,殊不知科學與民主的背後是以基督教的文化為根基。我們如何把這種精神文明最精彩的地方吸收進來?說到這著,我就想到「慈悲的主動性」,作為一種主動的本體可以跟人會面的時候,這就是基督教講的上帝,這可以從中國的角度把上帝講出來,不是通過外在的實體而講,而是從愛的本體,親情的本體來講。當然這著有一個前提,就是我講的基督教是指宇宙的本體是一個恩情宇宙,有一個有親情的真理,甚至對人類發出資訊。問題是人的心靈不能完全吸收這個上帝資訊,如何校正我們的接受器呢?那就須一種心靈開放,稱為信心,如此就可以碰到上帝,而產生崇高偉大的經驗。從這個角度來講基督教上帝,是從中國哲學角度來講,使之變成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若基督教信仰生根中國文化,其所涵具的平等、博愛、民主等等,均可以通過中國文化的特色來吸收,而不是原封不動搬過來。於是自由、民主、平等,均可在文化中生根,並且將其融進來,這大概也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一項重大工作。
𨪜𨪜二十一世紀宇宇宙論與宗教智慧
𨪜𨪜二十一世紀的思想我看還有一個很大的發展。當代科學的發展,一方面量子力學展示一個龐大整全而變化的世界,另一方面大爆炸論新證據,顯明宇宙有起源。從量子力學看,宇宙似是緣起生滅,其性本空,從宇宙起源看,又似有上帝創造萬物。從性空的方面在西方可以發展出虛無主義,但虛無主義不是文化出路,故此可能還要回到佛教所講的緣起,將當代人虛無的體驗變成空的體驗,空的體驗變成一種不執著的領悟,這就有正面價值。佛學也許對西方的虛無主義有些正面影響。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人過去講空很多,民間更講輪回,破壞性很大,認為現在的痛苦是前世造成的,不是現在的問題,就根本無法批判和改革現實社會。因為改革社會,必須強調社會的各種不正現象,不是自己前世造成的,而是因著種種外在的條件不完滿而形成,故須改革才能轉變。剛才提到的禪宗批判精神,對我來說還是有啟發性的,因為以前從來沒有人發展出禪宗作為社會批判的一種理據。我曾經在有關的國際學術大會上看到兩位佛學大師,一位是阿部正雄,是日本京都學派的禪學大師,也是我博士生時期的佛學教授,另外一位是日本的淨土宗代表,當時淨土宗批評禪宗一天到晚都搞最高領悟,不理這個社會,這也看出禪宗以前是不關注社會,是遠離社會的。我認為在中國禪宗變成對社會的批判,是一種很重要的發展。
𨪜𨪜評人人可成佛
𨪜𨪜另一方面,佛學常誇人人可以成佛,這觀點有時用得太濫,沒有嚴格的標準去判定怎樣才算成佛,結果會產生很多邪教教主自稱成活佛,或甚至騙人謂功力超過佛億萬倍。這種「自我無限化」成為一文化困局,使中國有學識的人很易自大自足,以為天下無敵。在一現代化社會,最重要的是人自承有限,在法治下人人平等。人的自我無限化是有很大危險的,一無限化就會把自己作為神,無權力者會創造邪教,有權力者成為暴君,產生無窮災禍。基督教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即誰都不能以自己為神,人人有平等,尊嚴和自由,但也有一個限定,不自稱淩駕他人之上,一限定的話,就可以彼此尊重了。不要以為我比你高,或者我包容你,中國的判教就是這樣,總想包容別人,看來是和平的,但總是把別人看得低一點。在多元年代來臨的時候,誰都須承認有限,誰都不能代表最後的真理,所以要尊重大家的不同,然後通過對話帶來和諧,中國將來應該在這方面有所發展。
𨪜𨪜倫理的根源在親情
𨪜𨪜在這種互相尊重而又和諧的精神之下,也帶來一種道德、倫理的重建,這是我最近關於中國文化思考最多的問題。我認為,也許禪宗精神可以破掉我們一些倫理上的執著,或僵化的教條,另一面,若要對社會的倫理確立一個根底,就需要宇宙的親情觀念,確立一切倫理為關係的根源,也就是說,宇宙是感通的宇宙,背後是個慈悲的本體,一個親情的本體,或稱為上帝。萬有是彼此感通的,人與人之間彼此相關,人與真理也是彼此相關,不只是獨立的個體,這樣才可以真正帶領出倫理精神。西方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但當代極端自由主義,又否定宇宙有真理,以虛無為本,人人背後也沒有宇宙的真理,結果形成獨我為本,你是你,我是我,個人主義變成自我中心主義,大家不能溝通,也不能對話。西方的倫理道德現在已經面臨崩潰,這是西方社會的嚴重問題。我總認為,中華民族與文化是人類倫理的最後防線,因為中國還沒有變到像西方那樣的個人中心主義,我認為在中國沒有變化到那一步之前,先處理解決,不要等走到西方那一步,然後把這個倫理精神重建。關鍵還在於關係感通的本體論的建立,這著面是以家庭作為最基本的單位,而不是以個人作為最基本的單位。以家庭為單位的倫理是以關係為本,是以親情為本,以感通為本。這樣的倫理關係也許可以避免個人自我中心主義,也不會變成整體主義對個人的壓制,以及個人主義變成虛無的。然後,我也想到佛教、禪宗在這方面可以作何種貢獻?禪宗對家庭倫理有何啟發?
𨪜𨪜重建中國的倫理道德
𨪜𨪜■:與禪宗本意相比,家庭倫理可能非常現實了,現在中國的問題就是道德倫理的重建問題。我經常說,中國的問題不是因為中國文化帶來的,而是恰恰因為丟了中國文化,所以,也只能用中國文化來重建中國的倫理道德。中國文化本身就是以道德倫理為本立國的。禪宗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一個是它的社會批判意識,否定精神,另一個就是菩薩心,也即佛教講的覺悟。菩薩心本身就是一種救世觀念,要把原來的超越變成參與,把出世的精神變成入世的精神,這著有理論的問題,也有很現實的問題。在主體這個問題上,其實佛教也受中國道家思想的影響,後來也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只是在一般情況下,中國人特別認為,把個體(從哲學或心理學方面思考)如何轉化為主體,又如何把主體和本體融合在一起,實際上經常是個體、主體、本體三者結合為一的,而這三者為一,這本體就是你剛才講禪宗時提到的慈悲,也像孟子講的測隱之心,不忍之心,憐憫之心。我曾經向別人講過,道德的激發往往比法律的作用強,法律制定再嚴密,總是有空子可鑽。舉一個例子,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經常挨餓,我往往是一個月的糧食只夠半月吃,有的同學從農村家著帶一些粗糧來,有人僅僅偷吃了一塊粗糧,結果一輩子羞於提起,這可見道德的力量之大。還有一件有趣的故事,王陽明有一個弟子,文武雙全,在家著抓到一個小偷,就要給他講良知一類的道理,小偷說,我是偷東西的,你還能說服我?這位弟子便命小偷把內外衣服全脫光,小偷就聽從了,最後又要他把內褲脫了,小偷不肯了,那位弟子便對他說,這就是你的良知了罷﹗這說明,無論什麼人,都還存在不同程度的道德潛力,道德作用是很強的。在禪宗著面,承認人的本體和個體是合一的,人性與天性是合一的,而這個天性就是超越,所以用這種觀念去建立人的道德,當然還有具體解釋善的一些戒律,如不能燒殺掠奪,姦淫,老百姓並不管太多的理論,但需要確立這些具體界定。紅樓夢中的王熙鳳說,我根本不信什麼因果報應,她為了一點銀子就可以殺人。所以我認為人只要有信仰,不管別人說是否迷信,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就曾聽到有的學者提出過要建立中華的基督教系統,這與你的觀點相似,畢竟還有中國文化的特點。事實上,基督教在傳入中國時候,受到很多排斥,在各方面都有問題,如何能化成中國式的即中華系統的基督教,這是一個很重大的課題。
𨪜𨪜心靈的自我反省
𨪜𨪜□:這也是二十一世紀人類發展中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當基督教從亞洲到西方,融合在西方文化中,經歷了很長時間。當基督教來到中國以後,如何融合在中國文化著,成為生根中國,屬於中國人的基督教,而中國文化又如何成為世界化,屬乎人類的資源,也許是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中國文化能對世界性的課題來說話,這也是我們這一代知識份子需要做的,不只是對中國本身問題,而且更是對人類問題,包括環境保護,新宇宙觀發展,還有社會道德倫理等問題。基督教中國化,中國文化世界化,這可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過程。另外,你剛才提到的倫理問題,我就想到耶穌有很後現代的一種自省倫理,在《舊約》是講十誡的,重視誡條,而耶穌則不用誡條教訓人。他在登山寶訓中提出,講什麼樣的人是有福的,第一就是虛心的人有福了,原文意指知道自己靈性貧乏的人是有福的,凡以為自己靈性或道德比人高的人,都心著充塞自大,不可能領悟宇宙神聖美善的國度,只有明白自己一無所是,心著面什麼也沒有,完全放開執著,謙卑自己,才可體悟上帝的福份。這個境界是很高的,不是單純講人不應該做什麼,而且虛心的人知天國,清心的人能見到上帝,承認自己貧乏的人,才能跟上帝溝通,這是一種很好的倫理精神。另外,當人用道德去論斷他人的時候,道德也可以變為道德主義,到處說別人不道德,本身就是一種很大的罪惡。中國在這方面也是很厲害的,道德的審判也造成了很多災禍,這就是所謂以理殺人。如何不以理殺人,耶穌在這方面表達了很高的境界,當眾人要用石頭打死一個姦淫的女人時,耶穌就問那些人,你們中間誰沒有犯過罪的,就可以用石頭打她,結果每一個人想想自己內心,同樣有罪過,不過沒被他人抓而已。人只要一自我反省,想到自己也有罪過,就不敢再隨意搬弄是非,論斷他人,且反而應該彼此寬恕彼此接納。這就顯明基督教的倫理精神不是一種道德條文,而是一種心靈的自我反省,這應該是一種自省的倫理精神。
𨪜𨪜■:說到這著,我就想到四川有一副對聯,百善孝為先,論心不論事,論事天下無孝子;萬惡淫為首,論事不論心,論心天下無完人,也是很說明問題的。
𨪜𨪜宇宙的感通性
𨪜𨪜□:這個很有趣。那麼,在提到感通的宇宙觀問題,我也想到華嚴宗「事事無礙」的精神,我總覺得量子力學當前種種新發現,顯示宇宙應該是彼此相關的,而且互相可以相通。這種宇宙的感通性在華嚴宗著比較強調,所謂「理事無礙,事事無礙」,視整體全法界都是相通的,《易經》也是這個精神,六十四卦就代表了整個宇宙的事相,這些事相都是彼此互相轉化和相通的。而基督教講的太初有道,這個道本身就是一種資訊,宇宙萬有不是亂來偶合可以產生,必須一開始(假如有大爆炸的話)就把一切安排好,這是一種資訊的安排。如果根據這個資訊的發展,萬有就變成一個有秩序有道的宇宙。資訊本來就有語言的意思,當然不是人所理解的那種語言,而是萬物背後那種感通的資訊。這麼看來,《聖經》的太初有道,華嚴宗的「事事無礙」,加上《易經》的生生不息,在強調感通的宇宙觀方面,可以彼此對話,而且顯然可以為人類共同的問題提供一種出路。
𨪜𨪜文化灌輸要落實在現實
𨪜𨪜■:討論下去,就涉及到人生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形象地提到一個例子:一個仙女從天上來到人間,給新出生的嬰兒帶了五件體物,分別是生命、歡樂、財富、高官、愛情等,還有死亡,他就選擇,一次選了歡樂,一次選了財富,一次選了高官,一次選了愛情,一次選了生命,每一次選,帶來的歡樂還之于痛苦,仙女感到很失望,就沒有什麼可以選擇了,只有死亡,不能不死。從終極意義上看,這似乎是有些悲觀,但死亡是不可選擇的卻是一個事實。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生命也不是可以選擇的,生不能選擇,死也不能選擇,禪宗所謂的隨緣,主要還是建立在生命這樣重大的基礎之上。我們現在談論的時候,有時還要落實到現實的問題上,比如剛才說的道德重建問題,就是一個重大問題。中國古代就有很多官員是反貪的,或者說,無論是基督教,還是佛教,伊斯蘭教,在反貪上總是有共同點的。前一個時期,我寫了一篇有關二十一世紀與佛教的文章,認為只要有貪污腐敗存在,只要有殺人越貨,男盜女娼,黨同伐異,只要有種種不良的社會現象,宗教信仰的存在總是有必要的,其中,我認為基督教傳播的要比佛教好,有自己的學校,有自己的學位,有自己的課程,更有自己的詩篇和歌曲。但佛教不一樣了,中國有一個李叔同,出身于清進士,也是個著名的近代和尚,懂音樂,會書法,採用外國歌曲配新詞作為學堂樂歌教材,他想用自己的才華宣傳佛教,但流傳不多,和基督教是沒法比的。所以,佛教的發展受到很多限制。很多東西是人類的淺層道理,物質的需要可以用科學技術來證明,深層的情感的東西只能通過宗教、信仰、理性來瞭解,這就是文化灌輸的問題了,也就是我剛才提到的要落實在現實的問題。
𨪜𨪜佛學末流的問題
𨪜𨪜□:如果不落實,一切都是空話,比如,如果法律定的再好,但大家不遵守,這就是人民的素質問題了。從中國文化來說,以前並沒有西方那種神聖的傳統,法律是政府用來對付人民的,是一種刑罰,做錯了就可以抓人罰人,但反過來,如果執法者不在場,人民就常常隨便來,沒有員警馬上不守規則,有了員警還可以通融走後門,與執法的人搞好關係,可以做不合法的事,這就是中國的問題。而在西方基督教傳統中,認為法律是上帝給予的,是上帝創造宇宙的自然法律,所有人間的法律都是從自然法引伸出來的,這個法律的神聖性是被肯定的。另一方面,西方基督教傳統在近代花了很大努力,去除教會末流的弊端,如天主教廷的異端裁判,及教廷代表上帝的無上權威,都在宗教改革後漸漸革除,回到原始的個人和上帝關係。當今佛教界也須面對其歷史流弊,如禪宗的「野孤禪」以為自己瘋狂亂來,就表現很高境界。佛學末流的危險就在於誰都以為自己的境界很高,稍微懂一點氣功的人,就認為自己成仙成佛,其實這本身說明並不真正懂得佛學。真正明白佛學的人,也知一切本緣起性空,既不拜偶像,也不自誇成佛。在基督教著面,如果認為很屬靈,論斷他人不屬靈,就不可能是屬靈的人,真正的屬靈的基督徒是永遠認為自己不是最屬靈的,且永遠謙卑,永遠開放追求和上帝的感通。但當人人可成佛的理論一出來,很容易使自己的人性膨脹。因為,見性可成佛,但又不能證明誰真成佛,然而當一些人宣稱自己成佛,或者一天到晚弄點小法術,很多人就信以為真,民間各種妖魔鬼怪就出來,臺灣和中國大陸都出了不少。另一方面,佛教末流講的隨緣也會變成不需要去做工作,守法不守法都一樣,因不是宇宙的真理,把人的生死看破,撞不撞紅燈就是小事了,這樣就會變成散漫的自由。本來是在具體世界任何地方都自在的一種隨緣最高精神,在變成可以證成自己不守法的依據時,種種問題就出來了。從前日本有一部電影叫「爭霸」,講一個武士,教一個幕府將軍的兒子殺掉父親,藉此繼承父位,否則,不殺死父親,父親會讓比他聰明的弟弟來繼承。但這位元大兒子根據孝道,認為不可以殺父親,武士就跟他講禪,說「見佛殺佛,見祖殺祖」,是超越善惡的精神。所以,對禪宗的歪曲可以變成這樣的違反倫常流弊。從這個意義上,使禪宗不陷於野孤禪,不走自我無限化及散漫自由之路,是其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課題之一。目前特別是面臨二十一世紀,儒釋道各大教均共同要面對文化的更新,須與西方現代與後現代文化對話,也須去掌握和體會西方精神文明的謙卑、懺悔、救贖等精髓,均應該是一當前文化的重大課題。
𨪜𨪜麻天祥:中國禪宗研究工作者。
𨪜𨪜梁燕城: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長
-----------------------
基督徒談「參禪」
〖「禪」是什麼〗 禪(Zen),梵語dhyana,又作「禪那」,意譯為「靜慮」,即靜息念慮的意思。在中國佛教,禪法被通稱的有兩種:即如來禪和祖師禪。如來禪者,如經論所說的四禪八定是,祖師禪者,經論之外,歷代祖師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的禪法是。 禪,以目前有許多人的競相 參與學習,可見它必然存在有相當大的魅力。因此綜觀它現時所顯示的現象,真是五花八門。雖然佛門教導「行、住、坐、臥」皆是禪。但基本上,只要提起「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打坐」。因為不管哪裡有掛名「禪」的道場,「打坐」必是一門自始至終的功課。於是以「打坐」為主的發展所及,「禪」,經由今人的詮釋產生了相當大的空間。 禪,於今時專以「打坐」為出發,就開展了繁多的種類;除了上述佛門自訕為正宗禪以外,禪修的境界,透過個人的冥思,就其目前已存在的眾多亂象,當務之急該先探討的是它們存在的價值,而不是只一昧判定「誰是誰非,孰正孰邪」。 禪,在中國,背負有千年傳統文化,因此融合了相當多的儒、道思想。基於「儒」,有人以「靜、定、安、慮、得」的「修心養性」來看待;期於「道」,有人歡喜「清淨無為」,或積極「修身練功」,其結果是共同皆以「禪修」自居。而另有一類較具現代資訊者,因國際文化交流普及影響,又有了更創新的作風:有人把它利用為「開發潛能」。也有人藉此自立新的宗門,招攬信徒,儼然成為新一代宗師。於是新興宗教,此起彼落,各家各派堅持己見,卻忙得信徒四處流竄,莫衷一是。普遍流行,乃因這種所謂啟發「本然自性」的說詞,最能迎合「人類自我」的高度訴求與滿足,或藉以逃避現實的挫敗與面對。 禪,在此先撇開它「起源於何」的定論;除了是為避免它反不得「自由自在」的限制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我們能重新正視思考「人的問題」。所以我們不妨先摒除「誰是正派」,「誰是外道」的爭論,而讓我們著重於探討:「禪,透過人,它真實是什麼?」所以,人藉由「禪」這樣的「靜慮」,它產生了怎樣的「冥思」,才真正是人人必要關心和明白的主題。 如來禪與祖師禪,佛門中人或許不認為有必要截然的劃分。僅就其個別特色,略作介紹: 「如來禪」:佛教經典裡的禪法,是如來所說,而依修法的不同,大致歸類了「三種禪」來認識,即「小乘禪、出世間禪、出世間上上禪」。 小乘禪:有五停心觀、四念處觀、八背舍、十一切處等: 五停心觀:能使五種過失停止於心的觀法,亦即聲聞乘人在最初人道時所修的五種觀法。 1)不淨觀:觀察一切根身器界皆屬不淨,以停止貪欲。 2)慈悲觀:觀察一切眾生痛苦可憐之相,以停止瞠恚。 3)因緣觀:觀察一切法皆從因緣生,前因後果,歷歷分明,以停止愚癡。 4)念佛觀:觀察佛身相好,功德莊嚴,以停止業障。 5)數息觀:觀察呼吸出入之相,每一出人,皆暗數自一至十,以停止散亂。 四念處觀:即 1)身念處:觀身不淨。2)受念處:觀受是苦。3)心念處:觀心無常。4)法念處:觀法無我。 以此四觀,使安住於道法。 八背舍:又名八解脫,即八種背棄捨除三界煩惱系縛的禪定。 2)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謂心中雖然沒有想念色的貪心,但是要使不起貪心的想念更加堅定,就還要觀想外面種種的不淨,以使貪心永遠無從生起。 3)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一心觀想光明、清淨、奇妙、珍寶的色,以使不起貪心,證得心性解脫,名身作證;又因此觀想能達於圓滿,安住於定之中,故又稱為具足住。 4)空無邊處解脫:略。 5)識無邊處解脫:略。 6)無所有處解脫:略 7)非想非非想處解脫:略。 8)滅受想定身作證具足住:略。 十一切處:又名十遍處即觀青、黃、赤、臼、地、水。火、風、空、識等十法,使其一一周遍於一切處。 出世間禪:若修次第三觀,先從假人空,次從空人假,接後空假雙離,入中道第一義觀,名之。 出世間上上禪:若於一法,圓觀空假中三諦,即空即假即中,非一非異,名之。 釋迦牟尼佛的修行證果,也經歷了四禪八定、五十二位次第等,時間長達三大阿僧只劫。 四禪八定:四禪是色界的四種禪定。八定是色界四禪定加無色界的四無色定(四空定)。 四禪者: 初禪:清淨心中,諸漏不動;有梵眾、梵輔、大梵等三天:此三天已不須段食,故無鼻舌二識,唯有樂受,與眼耳身三受相應,喜受與意識相應。 二禪:清淨心中,粗漏已伏。有少光、無量光、光音等三天:此三天無無前五識,僅有意識,因之唯有喜捨二受,與意識相應。 三禪:安穩{中,歡喜畢具:有少淨、無量淨、遍淨等三天;此三天識受皆與二禪略同,但意識怡悅之相,較為淨妙。 四禪:前五識具無、亦無喜受,僅有捨受與意識相應:有無雲、無生、廣果、無想、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等九天。 大涅槃經說,初禪天人,因心中仍有粗細思想,故外境有火災;二禪天人,於己禪定生喜樂心,故外境有水災:三禪天人,呼吸粗重,故外有風災;唯至第四禪,內外過患一切均無,所以諸災不至。 四空定者: 1)空無邊處定:修行者心想出離患難重重的色蘊物質的牢籠,於是捨色想而緣無邊的虛空,做到心與 空無邊相應。 2)識無邊處定:修行者以厭棄外在的虛空,於是捨虛空而緣內在的識,做到心與 識無邊相應。 3)無所有處定:修行者更又厭棄歧視,觀心識無所有,做到心與 無所有相應。 4)非想非非想處定:修行者進修無蠢想,做到如痴如醉無所愛樂清淨無為的境界。 五十二位次第:菩薩由凡夫到成佛,一共要經過五十二個階位,即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十信是由十住中的第一發心住另立為十。其中十住、十行、十迴向,稱為三賢,是資糧位:十地又稱十聖,是修習位。論時間,須經三大阿僧只劫。 三大阿僧只劫:菩薩修行成佛的年數,極多,無央數。 修行次第歷經五位、五十二階,初阿僧只劫在資糧位有十住(第一發心住,包括十信,由凡夫修十信成就,須經一萬大劫。)、十行、十迴向,在加行位有修成四尋思觀的暖、頂二者,與修成四如實智的忍、世第一二者。第二阿僧只劫有在通達位(即見道位)的初地人心,與在修習位(即修道位)的初地住心、出心及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第三阿僧只劫有在修習位的八地、九地、十地、等覺,及究竟位的妙覺。 佛法浩瀚,法門八萬四千(略數,表極多),光是教理,無人終其一生能參透、證果,所以若不能確定「三世輪迴」之說,佛法的可行性與存在價值,是有待商榷的。 「祖師禪」:自菩提達摩東來傳慧可,傳弘忍等,禪法在中國有了「教外別傳」。因礙於佛祖年代久遠、地源遙隔,以致產生有關佛經不完備或真偽的議論 ,乃轉而重視佛法「自覺體驗」的事實,認為佛法當落實於人人自心的體悟自證,非必由「言教」,於是演變成為「不立文字」的「以心傳心」。傳惠能,「直指當前一念即解脫自在(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為達摩禪的中國化開闢了通路,至魏晉以降,更老莊化、玄學化。現前佛教中人雖一再言明從「印度禪」演化為「中國禪」,實質還是一貫的「如來禪」。但以中國人一向認為自己中原文化博大精深的自信,對外來宗教豉哲學思想多半是先予包容,再加以雜揉,而後傳流。佛學承傳期間雖有東晉釋道安重申「以經解經」的教訓,但普觀現在「類佛教」的亂象,乃因歷代以來,「九流十家」的思想已然與中國佛教信仰混然相融,所以今時人的「禪修」,行者慨然標榜目證境界的不同凡響之際,是該當小心考量此境是否只是原有思想背景與知識教育的投影,或有其他我們未知或非人的能力範圍所能掌控的存疑等等。 我們不定要「以古非今」,或斷言「今不如古」;好人、壞人,古今皆有,再看出土古文物的發現,在在顯示了遠古的高度文化,不禁令人懷疑人類文明是否進步了?「進化論」之說又怎能視為不變的真理。而能確定不易改變的是人性:人性裡有善有惡。禪家說要「明心見性」,探究「本原天真自性佛」。千年以來,除了述說於釋迦牟尼佛的冥想世界以外,「禪門公案」又添了幾則類似「狗子有佛性也無」的啞謎,於是尚未「明心見性」以前,倒先留下一則蘇東坡--「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注1)的真話。 ------------ 注1.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八風者,指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八事。此八事能引發世人愛、憎之心,故以風為喻、稱為八風。傳言宋時蘇東坡與僧人佛印交好,兩人常論禪說道。蘇東坡一生宦海浮沈,自揣己練就「金剛不壞」,一時興起,提筆寫了五個字,命書僮送與佛印認證。佛印看罷此五字,在旁寫下兩個字,交與書僮送回。蘇東坡獲看此二字,氣呼呼地直要過江來找佛印理論。其時,佛印早已等在江邊,一見蘇東坡即哈哈大笑,並說:「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原來蘇東坡寫的五個字是「八風吹不動」,佛印回給他的兩字是「放屁」。論此「八風」,其實就世法而言:即利哀、毀譽口、稱譏、苦樂的相對;處此世間無常的相對,謂以「佛性」、「如如不動」能有絕待義。上論雖是,幾人能行?一句「放庇」,立時就亂了方寸了 ------------ 〖「禪」與基督教的「靈修」〗 禪,說穿了,不過是人自我的見證:人人都可以有見證;人的自我觀照下的見證,充其量最高者也不過是釋迦牟尼佛--「華藏莊嚴世界」的幻象。《楞岩經》裡教修「如來大定」,歷經「五十陰魔」,佛警戒禪修者對於每一次自證的境界要常有這樣的心態--「暫得如是,非為聖證,不做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因為「汝輩修禪,飾三摩地,十方菩薩及諸無漏大阿羅漢,心精通昏,當處湛然」。所以禪修者有境界,最忌「著相」--《金剛經》有云:「若以色見我,若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禪家視自證的境界如夢如幻,才能一重一重步人更高的悟境,所以禪者,乃為解甚深又甚深密意。個中的神秘對人極具高度的吸引力,推想這可能是「禪」給人的最大魅力。 所以任何人於「禪修」產生了莫大的好奇,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人類自我探究內心深處的本能,是源自「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原文是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傳3:11 ) 永生的盼望既已存在人的心中,人一日不得「永生」的真理,他就不會停止一日的探索。又「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林前2:9 ) 因此禪,通過meditation的體驗,不是任何宗教的專利,藉此要提醒大家仔細思考的是,做這樣的功課,其動機與目的何在?或許有人一開始真是為內心因於「未知」的驅動,也或有人是因看到世界的無常、苦惱與虛空,而亟需尋求出路,更或有人直接就是要探究「永生」。但人類畢竟是軟弱的,他們常常就敗在中途上:在禪修的過程,孤單的自我,最容易掉人小小輕安的陷阱或初步的幻境裡:因為這大符合人類「自以為是」的個性,同時也轉換了人在現實世界裡「求不得的苦」。 或許有人能自我要求「時時放下、步步提升」,然而也不過是落入一個更讓人不願離開的「無止盡遊戲」中。但縱然「禪修」會發生這樣的危險,而我們也不是就因此要扼殺人這樣的本能。所以在此與基督徒談「參禪」,卻是希望我們能更善用發揮這樣的本能,喚醒我們當要常注念神賜給我們的「永生」,努力不懈地「追求真理」。且要以此作為生命的動機與目的,則我們「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約3:21 ) 「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林前2:1O) 冥想(meditation),內心觀照,產生的境界是可以浩瀚無窮的,給打坐人的幻想力可真是「天馬行空」;特別對一個不信仰獨一「三一真神」的人,更是充滿了詭譎、神秘的懾受力。的確,「水往低處流、人住高處爬」,這話對人是有相當的鼓舞作用,但人卻要謹慎不讓自己成為「好高騖遠」。有史以來,人類探索「未識的」,的確幫助人開拓高度的智慧,但是「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 」(林前:11)「未識的」未必都是良善的,尤其考量到人的深重罪性,透過「打坐」的途徑,是人心在內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的,真的是危機四伏,不會處理可能就「走火人魔」,落人極度的執著,自誇自己獨有的功夫境界,自得於自己的超凡入聖。此時的他,志得意滿,卻不知仍是「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人才能看透。」( 林前2:15 ),走進這樣的地步,往往無以自拔、無人能救。 人的自我努力本是值得褒揚的,奈何人的罪性深重。佛法的《百法明門論》說人有「六大根本煩惱」,貪、瞠、痴、慢、疑、不正見;「八大隨煩惱」,忿、恨、惱、覆、誑、諂、憍、害、嫉、慳。「二中隨煩惱」,無慚、無愧。「十小隨煩惱」,不信、懈怠、放逸、昏沉、掉舉、失念、不正知、散亂。思想人要依靠自我修行來出離我的深重罪惡,這會是多麼困難的一個負擔,甚且徒勞無功。的確如保羅所言的: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作的。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原文是人),我是喜歡神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月兌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羅七:18-25 ) 所以想靠自己修行來「了生脫死」,根本是自討苦吃,糟蹋了有生的年歲。如今,唯我們已經接受了有完全的義的主耶穌基督的救贖,才能白白得了永生(佛法希望修成的「了生脫死」)的恩典,因為: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貝易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3:16 ) 「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足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羅八:l一4 )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同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 羅3:24 ) 甚且我們能藉由在主前禱告靜默,從神支領許多意想不到的智慧及領悟。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西1:9)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神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並且我們講說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心或作:將屬靈的事講與屬靈的人J」(林前二:12-13) 「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他呢?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了」。(林前二:15-16) 感謝主,讚美主,成為神的兒女真是何等幸福;因我們所信靠的神,他「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裡面藏著。」( 西2 :3 )且「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箴1:7 ) 所以人想要向更高的境界去參究,在人自己的領悟裡是有限的、危險的。而唯一心能向著神的,神必然教我們得的更多,因為神的兒女有這樣的權柄,「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據去的,可以醒悟,脫離它的網羅。」( 提後2:26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聯絡,以致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們真知神的奧秘,就是基督。」( 西2:2 ) 堅信我們的主愛是完備的,要成為蒙福的基督徒,最重要當常建立這樣的信靠,不住向神靜默禱告說: 「您的手製造我,建立我;求您賜我悟性,可以學習您的命令。」( 詩119:7 ) 「耶和華啊,願我的呼籲達到您面前,照您的話賜我悟性。」( 詩119:16 ) 「求您賜我悟性,我便遵守您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 詩119:34 ) 「我是您的僕人,求您賜我悟性,使我得知您的法度。」。( 詩119:125 ) 「您的法度永遠是公義的;求您賜我悟性,我就活了。」。( 詩119:144 ) 是的,我們要「側耳聽智慧,專心求聰明,呼求明哲,揚聲求聰明,尋找他,如尋找銀子,搜求他,如搜求隱藏的珍寶,你就明白敬畏耶和華,得以認識神。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給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給行為純正的人作盾牌,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護庇虔敬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義、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靈要以知識為美。謀略必護衛你;聰明必保守你。」(箴二:2 -11) 我們向著神唯一道路的「靈修」,勝過一切「參禪」。除了 神以外,我們真是再也別無所求了。
-----------------------------------------
基督徒的襌1
劉賽眉
聖誕節前,一位朋友送給我四本靈修書籍,我隨手翻閱了各書的前言,其中一本名為「基督徒的禪」(Christian Zen, by W, Johnston S. J. ) 引起了我濃厚的興趣,遂騰空了幾個晚上,手不釋卷地把它唸完。最近,在香港的公教報上又得知該書的作者訪港並作神修講座及輔導,筆者遂願以微薄之閱讀心得,推薦此書與有志研究東西方神修特色,並有興趣於從事神修事務者。
首先,對該書及其作者作一簡略介紹:作者張斯敦為愛爾蘭人,耶穌會士,居日本二十餘年,專心研究東方神修及文化特色,習行禪宗不輟,曾隨名師學禪,頗有所悟;執教於日本東京上智大學,為神學教授,著有神秘學及神修書籍若干 ﹙著作名稱參閱公教報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一版﹚,對中古神修頗有研究。
至論「基」一書只有一O九頁﹙包括一附錄﹚;封面之設計,即令人產生東西文化在基督宗教內融匯的感覺。該書大部份自作者本身之經驗出發,集東西兩方文化及神修特色於一身,文無矯飾,簡樸坦率,思想明朗,風格平實而稍帶幽默,讀之使人趣味盎然。
該書分為十一章及一附錄。第一章:自述其習禪之始;第二章:對談;第三章:一元及二元;第四章:基督徒的禪﹙之一﹚;第五章:基督徒的禪﹙之二﹚;第六章:基督;第七章:公案語錄;第八章:身體;第九章:呼吸的節奏與祈禱;第十章:進展;第十一章:悟;附錄:姿態。
從第一章開始,作者便毫不隱諱地敘述他在日本學禪的經過,從他簡略的描述中,讀者可以窺見日本目前禪宗發展情況。在日本某些地方建有寬大的廟宇,作者亦曾廁身其中習禪。他認為基督宗教之所以不能夠在亞洲地域生根植基,乃是由於未曾苦心向當地的文化及各大宗教學習;他更認為,若基督宗教輕忽像禪這一類的東方文化遺產,甚或對它採取敵視的態度,則基督宗教很難披上亞洲人的外衣,穿上亞洲民族的心態而成為一地道的東方基督宗教。
當作者學習打坐時,他發現這些默觀的方法為他並不新奇,聖十字若望早已用類似的方法默想。習禪之初並不容易,特別為長期受西方教育,受西方傳統文化薰陶的傳教士。一般而論,西方著重推理,在默想中習慣定像,若空其思想與圖像,必須格外下工夫。作者告訴我們一個不可忘懷的經驗,那就是他第一次參與坐禪﹙類似我們的退省,通常為期七天﹚;參與坐禪的人必須早上三時起床,打坐十次,每次約四十分鐘,直到早上九時才休息。最有趣的是每頓飯也在打坐的房內,即使用飯時亦不改打坐的姿勢。在坐禪中也有「講道」的部分,每晨由一位禪師講解佛家的哲學原則並訓示習禪的實際方法,此外,尚有所謂「個人輔導」部分,輔導的禪師聲明,在個別輔導中,他所關心的只是您習禪的經過及如何打坐,對於其他問題,如:經濟、家庭、心理……等問題他一概不管。在這一次的坐禪中,作者又從禪師那裡知道了其他宗教內也有禪,只是禪師稱其為「不正統的禪」。作者在這次坐禪中也接受了個別的輔導,他與那禪師的對話亦十分有趣,現節譯如下:
禪師:「請告訴我您如何學禪?您在打坐時做些什麼?」
作者:「我想,我所做的就是您所謂的不正統的禪。」
禪師:「很好!很好!許多基督徒也是如此,可是,您如何懂不正統的禪?」
作者:「我所指的不正統的禪,就是面對天主而默坐,無言、無思想、無圖像、……」
禪師:「您的天主無所不在嗎?」
作者:「對的!」
禪師:「您感到自己在天主內嗎?」 ﹙被天主所包圍﹚
作者:「不錯!」
禪師:「您真的經驗到如此嗎?」
作者:「是的!」
禪師:「很好!很好!就這樣繼續下去吧,到最後您會發現天主消失了,只剩下
您!」
本來,在這樣的對話中,被輔導者不應當反駁禪師的,但作者卻因禪師這話而驚訝,在我們的傳統神修上只聽過說:自我完全消失而只留下天主,而未曾聽過說天主消失而只剩下自我的。作者於是對禪師說:「天主不會消失,消失的是我,而不是天主!」禪師答說:「對!對!都是一樣,這也是我的意思!」
作者離開禪師之後,內心覺得禪師的話使人大惑不解,後來經過他與友人談論,知道在禪內是沒有二元的,到最後天人合而為一,達到物我兩忘之境,因此,天人合一是禪﹙或默觀﹚的最高境界。
當作者與他的禪友不斷地交談之後,他發現禪內並沒有 Martin Bouber 所謂的您—我關係,為他們沒有「神—人」,無「他」、亦無「我」,只有「一」。
作者在第三章中詳細解釋一元與二元的神修。他認為在佛教裡沒有二元的思想,但在基督宗教內一元與二元的思想並用:他以為一元與二元只是受造物經驗到造物主的兩種不同方式;在聖經中兼備一元與二元的的神修概念。的確,在古經中多次見到「您—我」的位際關係,天主猶如人一樣地與人交往,這位際關係在 「盟約」的概念中特別明顯;在二元的神修概念下所產生的後果很自然就是神與人的交談,對禱、奉獻……等。但在聖經中我們同時可以找到另一種一元的神修概念,譬如說:「祂在我內,我在祂內」、「穿上基督」……等,在聖保祿和聖若望的著作中,一元的思想俯拾皆是。作者認為基督徒的祈禱達到高峰時就不再是「我與天主」的交流,而是「基督在我內與父」的交流;換言之,真正的祈禱不再是我的祈禱,而是基督的祈禱,是基督在我內呼喊:「阿爸!父啊!」在這樣的祈禱中,自我完全消失,消失在基督內。其實這也是尼西‧額我略和聖奧斯定的神修——天主在人心的最深處。
由此看來,禪宗的一元思想與基督宗教的神秘家的一元經驗實在有可接觸和共通之處;同時,中古的神秘學也訓示走神修道路的人必須經過靈魂的黑夜,也就是說不用理智、思想去認識天主,而只用直觀和心去接觸天主。
當作者談到基督徒的禪的時候,他以為即使為那些對禪並沒有成見的信徒也會有困難,其困難源於兩點:﹙1﹚在禪中天主的地位;以及﹙2﹚在禪中基督的地位。關於這兩點困難作者都分別有所交代。在第四、五兩章,作者又談到禪的性質以及禪對現代東方信徒的意義。作者認為,按「禪」這字頗有「默想」之意,無怪乎那位禪師說一切宗教內皆有禪,但這「默想」並非是在理智層次上的推想,而是指心靈的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中的人能夠意識到或洞察到一切事物的本質,這種意識延長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亦可以說禪就是生活,就是工作(2)的默想並無一客體的對象,主要是返回整個人存在的深處。作者還以為,禪為現代的神修學有「剔秘」(demythologize)的作用。過去在猶太基督徒的傳統中,一切均以神為中心,用神去解釋一切現象,譬如說天下雨了,就說是神的作為;又譬如說人走向邪惡就說是神使人心硬……等等。但是,在今日俗化的社會中,一切以人為中心,再也不能接受這套以神為一切現象的原因的解釋,而禪則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方法,它只要求人相信獲得佛性和達到覺悟是可能的;在禪裡人只管跟著指示去打坐,努力達到「空」而至於大覺大悟。
公案語錄是禪宗很重要的因素,在第七章中,作者解釋何謂公案語錄,並把它與基督宗教的啟示﹙或更好說是聖經﹚作一比較。公案語錄是一些著名的禪師用以開啟其弟子的言語,通常是一些似是而非、既非又是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能用理智去解決,一切邏輯都對它朿手無策,只有當人此公案,忘記自我,到最後甚至把公案也忘掉時,才真正達到解決之途。人面對這些似是而非,既非又是的問題必須經過一番掙扎和奮鬥,而公案語錄最後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引人進入覺悟之境。有時候,這些問題表面看來非常的不合理,難於了解,甚至於近乎瘋狂,但它卻能收到淨化和獲得智慧的效果。
作者更把我們的聖經言語與公案語錄作一比較,他認為在福音中含有豐富的「公案語錄」,譬如說:「讓死人去埋葬死人,但你來跟隨我!」「那喪失性命的得到性命,那得到生命的喪失生命」;「這是我體我血」……。難道這些話不是超出人的理性、難於了解,甚至近乎瘋狂嗎?然而,信仰卻能穿透這些言語;只當人在信仰中接受這些話,並謙誠地實踐的時候,他才會深深地了解並經驗到這些話的真實性。有一位禪師說:如果基督徒知道如何去讀他的聖經,他們也能夠從這些話中「覺悟」。在基督宗教內破此「公案語錄」的不二法門就是基督徒的深度信仰﹙信德之光﹚。
東方宗教對人的身體甚為重視,一切宗教經驗均由人的身體出發。所謂默觀就是一種教人如何運用五官、以及其他官能的藝術(3);對於進行默想的地方也甚為重要,必須選擇;習禪的人大多數相信禪能裨益人的心身健康。 作者認為,這去我們的神修也相當注重人的身體,如果想度一默觀的生活則必須控制五官及言行舉止,這種德行統稱之為「節德」。在禪裡節制是非常重要的德行,雖然其強調方式與我們有別。此外,基督徒傳統的神修學也曾談到,度默觀生活的人身上常發放著恩寵、喜悅、與平安的光輝,因為在默禱中天主的光榮滲透了默觀者整個的存在。
在此,我們可見不論佛教與基督宗教都認同人的得救是整體的;人雖然是精神與物質的結合體,但救恩卻透過精神而進入物質,物質到最後變成了表達精神的標記,這也就是所謂的「誠於中,形於外」「。對於「身體」在禪中的地位,作者在第八章中有更詳細的闡釋。
論到人的呼吸,在東方人的思想中,它具有特殊的意義,人的呼吸不只是人身體的一種功能,它與宇宙的生氣息息相關,故此,若人使呼吸均勻有節,就意謂使自己與整個宇宙及一切生物的關係和諧有序。在猶太基督徒的傳統裡,呼吸與氣和聖神有關,這「氣」充滿宇宙。習禪者很注意呼昅的調節,呼吸的節拍不僅有助於人的修養,而且能幫助學禪者漸漸更深地進入內心;一般而論,像「南無阿彌陀佛……」等短句能夠幫助呼吸的節拍均勻;此外,在第九章裡,作者還說,當人動、生氣、以及有其他偏情時,呼吸會變得較為疾速而不均衡;但當人心平氣和、安謐寧靜之時,呼吸會比較緩慢而有節奏。
事實上,聖依納爵所著的「神操」中有「第三式祈禱」(4) 就是教人如何祈禱與呼吸的節奏相配合,其目的在使禱詞中的意義深深地滲入祈禱者的意識中。我們平日所誦唸的玫瑰經也有這樣的作用,可惜今日的人漸漸已忽略了玫瑰經,其實,倘若慢慢地誦唸,單就修養方面而言,它的價值就不可抹煞了。
談到禪不能不談「悟」,「悟」是整個禪的軸心因素,習禪的人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悟,但亦可能終生坐禪而毫無所悟,這並不意味著他的努力徒勞無功,因為坐禪本身就是悟的一種形式,就如聖十字若望所說:默想中的黑暗本身就是「悟」。為聖十字若望而言,無思想、無概念的黑暗就是信德,信德就是光。
基督徒在打坐中是否也可能達到佛教所謂的悟?作者把「悟」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屬於人性的,就如柏拉圖是一個例子:第二類的悟特別屬於猶太基督徒,聖保祿在大馬士革的經驗以及梅瑟在不焚荊棘中所經驗到的皆屬此類;第三類則是所謂的「悔改」,悔改的意義首先是指心靈的改變,悔改者猶如瞎子復明,看見了天主的光榮。初期教會的宣講常常導人走向此內心深處的皈依,就仿彿禪師引導弟子達到悟的境界,然而,這「悔改」與禪宗的「悟」不盡相同,作者主要的意思是指:倘若基督徒採用禪的方法,在信仰及禮儀的氣氛中,這禪能夠幫助基督徒深深地進入悔改的喜樂。最後,作者更把禪的一些因素與現在流行的聖神同禱運動中的某些現象互相比較,讀者在書中的第十一章可窺見一斑。至於本書的附錄全在說明各種不同的打禪姿態,並有插圖加以說明,十分清楚。
最後,筆者所以願意介紹此書,並非因為它談禪談得特別好,雖然我們並不否認作者對禪實在有相當的研究和身體力行的經驗。無論如何,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東西兩方文化和神修的相遇,也看到了基督宗教如何淨化及補充了禪學中之不足;主張芸芸眾生皆可擁有佛性的禪學,其一元思想常有瀕於泛神論之危險,而基督宗教啟示中的二元概念﹙位格關係﹚則可防止泛神的弊端;至於禪學中的悟,非常強調人的努力,而基督徒的禪雖然也很注意人的勞苦,但到底使人達到「悟」的境界的是信仰,而信仰又是天主的白白的恩賜,非由人之功勞所邀得。無可否認,禪為東方人誠然是一種較適合的默觀方法。按筆者所知,最近某地方亦曾用打坐的方法舉行退省,據參與此退省的一位朋友反應說,坐禪的確幫助人集中精神、收歛、使人比較容易全神貫注地體驗到天主的臨在。
就如作者所說,如果中世紀的基督宗教能夠接受亞里斯多德的思想範疇、言語和概念等來表達基督的訊息,而造成中世紀的一段輝煌歷史,難道基督的信仰就不可能在二十世紀以及往後的日子裡,利用東方人的思想型態和文化遺產開創一頁與中世紀同樣燦爛的歷史嗎?
---------------------
李四龍/文
禪在西方的傳播,當然首先要歸功於鈴木大拙(D.T.Suzuki,1870—1966)的努力。1927年他以英文發表的《禪佛教論集》(Essays in Zen Buddhism),在西方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八十年過去了,西方人對“禪''的認識與研究,已不再停留於鈴木所介紹的日本臨濟禪,而是覆蓋了佛教裡所有的禪修傳統,中國的禪宗成為最受關注的對象。久而久之,東方的禪法融化到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里,漸漸烘托出一個目前還模糊不清的“基督禪”(Christian Zen)輪廓,開始了佛教在西方社會漫長的本土化歷程。因此,“禪”對東西方思想的和會溝通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基督禪''早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經有人提出,迄今已有近40年的歷史。這並不代表一種新的禪修方法,而是表明了東西方兩種不同宗教之間的溝通方式。基督禪是為西方的基督徒而設的,卻沒有讓他們放棄基督教的要求,有的牧師甚至還想讓東方的基督徒藉此更好地理解西方的基督教。
一、從神秘主義到宗教對話
為了使從不了解禪宗的西方人理解什麼是禪,鈴木以“神秘主義”搭建禪與西方宗教文化的橋樑。他有一部專著,題目就是《基督徒與佛教徒的神秘主義》(Mysticism in Christian and Buddhist)。鈴木非常重視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1260—1327)的神秘主義思想,認為禪與基督教的默禱比較接近,坐禪類似於基督教的“靈修”,雙方都有神秘主義的因素。之所以會把“禪''意譯為英文的meditation,原因是該詞經常和基督教所講的“靈修”有聯繫。艾克哈特是德國多明尼哥會教士,他的思想融合了新柏拉圖主義、阿拉伯及猶太哲學,是基督教神秘主義傳統的代表人物。神秘主義(mysticism),有時也被譯為“冥契主義”,這種譯法或許更能反映它的特質。這種宗教哲學,主張要在靜默之中祈禱,實現與天主的合一。在鈴木之後,久松真一(1889—1980)、西谷啟治(1900—1990)等京都學派第二代學人,都會在他們的談話、著作裡重新提到這位德國神秘主義哲學家。
受到鈴木著作的影響,歐洲的宗教學者,最初幾乎都把“禪”當作一種神秘的冥想傳統。奧托(Rudolf Otto,1869—1937),是20世紀最重要的神學家、宗教學家之一,在《論神聖》(1deao of the Holy)、《東西方神秘主義》(Mysticism East and West)等書中,斷然否認禪是一種哲學,反對用西方的哲學理論來詮釋禪悟。在他看來,頓悟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神秘,開悟的時候,修行者既無法自知,也無從預知。
以神秘主義作為佛教與基督教對話的契機,鈴木進而闡發佛教的根本思想——空。他曾與默頓(Thomas Menon)進行了一場名為“空的智慧”的對話,登載在1961年紐約《新方向》雜誌上。鈴木認為,猶太教與基督教的“無垢”可以看成佛教“空”義的道德化,而它們的“知識”概念相當於佛教所說的“無明”。《聖經》講人吃了禁果以後,獲得二元對立的“知識”,禪師是要除去從“知識”所生的一切污穢
-----------------
李四龍/文
禪在西方的傳播,當然首先要歸功於鈴木大拙(D.T.Suzuki,1870—1966)的努力。1927年他以英文發表的《禪佛教論集》(Essays in Zen Buddhism),在西方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八十年過去了,西方人對“禪''的認識與研究,已不再停留於鈴木所介紹的日本臨濟禪,而是覆蓋了佛教裡所有的禪修傳統,中國的禪宗成為最受關注的對象。久而久之,東方的禪法融化到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里,漸漸烘托出一個目前還模糊不清的“基督禪”(Christian Zen)輪廓,開始了佛教在西方社會漫長的本土化歷程。因此,“禪”對東西方思想的和會溝通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基督禪''早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經有人提出,迄今已有近40年的歷史。這並不代表一種新的禪修方法,而是表明了東西方兩種不同宗教之間的溝通方式。基督禪是為西方的基督徒而設的,卻沒有讓他們放棄基督教的要求,有的牧師甚至還想讓東方的基督徒藉此更好地理解西方的基督教。
一、從神秘主義到宗教對話
為了使從不了解禪宗的西方人理解什麼是禪,鈴木以“神秘主義”搭建禪與西方宗教文化的橋樑。他有一部專著,題目就是《基督徒與佛教徒的神秘主義》(Mysticism in Christian and Buddhist)。鈴木非常重視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1260—1327)的神秘主義思想,認為禪與基督教的默禱比較接近,坐禪類似於基督教的“靈修”,雙方都有神秘主義的因素。之所以會把“禪''意譯為英文的meditation,原因是該詞經常和基督教所講的“靈修”有聯繫。艾克哈特是德國多明尼哥會教士,他的思想融合了新柏拉圖主義、阿拉伯及猶太哲學,是基督教神秘主義傳統的代表人物。神秘主義(mysticism),有時也被譯為“冥契主義”,這種譯法或許更能反映它的特質。這種宗教哲學,主張要在靜默之中祈禱,實現與天主的合一。在鈴木之後,久松真一(1889—1980)、西谷啟治(1900—1990)等京都學派第二代學人,都會在他們的談話、著作裡重新提到這位德國神秘主義哲學家。
受到鈴木著作的影響,歐洲的宗教學者,最初幾乎都把“禪”當作一種神秘的冥想傳統。奧托(Rudolf Otto,1869—1937),是20世紀最重要的神學家、宗教學家之一,在《論神聖》(1deao of the Holy)、《東西方神秘主義》(Mysticism East and West)等書中,斷然否認禪是一種哲學,反對用西方的哲學理論來詮釋禪悟。在他看來,頓悟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神秘,開悟的時候,修行者既無法自知,也無從預知。
以神秘主義作為佛教與基督教對話的契機,鈴木進而闡發佛教的根本思想——空。他曾與默頓(Thomas Menon)進行了一場名為“空的智慧”的對話,登載在1961年紐約《新方向》雜誌上。鈴木認為,猶太教與基督教的“無垢”可以看成佛教“空”義的道德化,而它們的“知識”概念相當於佛教所說的“無明”。《聖經》講人吃了禁果以後,獲得二元對立的“知識”,禪師是要除去從“知識”所生的一切污穢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