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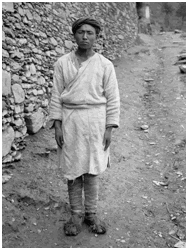
葛維漢
葛維漢 (英語: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年3月21日-1961年9月15日),美國著名傳教士、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
葛維漢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3mraBUn
生平
葛維漢出生在美國阿肯色州的小鎮,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1911年作為優秀傳教士、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前往中國。1932年到1948年,他被任命為成都華西協合大學教授,負責文化人類學和考古學的課程。除此之外還擔任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長期在中國西南地區從事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和博物館工作,幫助很多的當地社區和邊疆地區保護並記錄了他們的宗教、廟宇和風俗習慣。對中國西部土著民研究作為卓越的貢獻。[2]
1962年9月15日葛維漢在美國科羅拉多州逝世,享年77歲。
葛維漢研究
2010年5月10日,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霍巍教授以及考古系主任李永憲教授,應邀赴葛維漢博士母校華盛頓州惠特曼學院及西北檔案資料館考察並查閱了其相關舊藏資料。[3]
----------------------------------------------
陶倫士
----------------------------
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学家可能隐瞒了‘三星堆’研究”和“中华文明可能是来自于西亚文明”? - 知乎 https://bit.ly/2PHxCqb
--------------------------------------------------------
中國邊緣的再建構:由蠻夷到少數民族
講題: 中國邊緣的再建構:由蠻夷到少數民族
講者: 王明珂先生((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時間: 2002年06月29日(本館系列演講)
中國邊緣的再建構:由蠻夷到少數民族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https://bit.ly/3mrX27l
蠻夷是……猺、獞/非我族類/應被驅逐於中國疆界外/醜陋粗壯的男子
少數民族…傜、侗/兄弟民族/應在中國國界內/美麗妙曼的女子
蠻夷是華夏邊緣
至少自漢代始,華夏便自稱「中國人」。此一自我稱號,意味著「居於四方蠻夷環繞之中的文明人」。因此在自稱中國人的華夏眼中,那些居住在邊疆的非漢族是「異族」,他們就像是華夏心目中「我群」的邊界。強調這些異族的「異類本質」,也是在強調在此「邊緣」之內的華夏間的「同質性」。數千年來,華夏一直以描述這些非我族類的奇風異俗,以及從事並記錄華夷間的戰爭,來維持並強化這個族群邊界。
近代華夏邊緣的再造
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國族主義」、相關的「民族」(nation)概念與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隨著歐美列強的勢力傳入中國,並積極爭奪中國及其周邊「藩屬」地區的資源。在憂心西方列強的擴張,並深恐「我族」在「物競天擇」下蹈黑種與紅種人受人統治之後塵,中國知識分子結合「國族主義」概念、民主改革思想,極力呼籲「我族」應團結以自立自強。這個「我族」,特別是在革命派人士心目中,指的是「漢族」。在較能包容滿族的立憲派知識分子心目中,我族則包含滿、蒙等族。後來,在歐美列強積極營謀他們在西藏、蒙古、東北與西南邊區利益的情況下,結合「中國人」(核心)與「四裔蠻夷」(邊緣)而成「中華民族」的我群想像,逐漸成為晚清與民國初年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國族藍圖。
這個國族建構,主要賴於建立這個大民族的「共同祖源記憶」(民族史),以及因此建構新的「華夏邊緣」(少數民族)來完成。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民族史」研究,以及「邊疆民族」調查研究,可說是這「華夏邊緣」再造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
由蠻夷成為少數民族:羌族的例子
由清末到民初,岷江上游地區「羌族」與「藏族」之間的分野,並不是一直都很明確,而是有一個由模糊而漸清晰的過程;這就是「民族化過程」。在此過程中,各種「外人」--如中國邊政官員、西方學者與傳教士、從事西方新學術研究之中國學者--與不能算是外人的土著知識分子,帶著新的「民族」與「文化」概念深入觀察、理解土著。他們對土著的新理解,包括分類命名及其歷史與文化,透過文獻、口述等社會記憶媒介成為民族知識,而影響中國官方對岷江上游土著的識別與分類,也影響土著的自我認同。
1915年陶倫士(Rev . Tomas Torrance)
他深愛他的教民們,也對他們的文化習俗及其來源深感興趣。由於將羌民宗教視為一種「一神教」,因此他認為這民族是古以色列人的後裔。
他對羌民服飾的描述,特別強調當地人所穿的白色長衫。他說,大部分的羌民「仍」穿白色麻製衣服,而且他推測過去「曾經全都如此」。他認為尚白、潔淨,以及以白為善,這都是以色列人的習俗。陶倫士指出有些地區羌民婦女配銀環為頭飾、耳飾,而在巴勒斯地區Ramallah 婦女頭上也有配戴銀幣飾的習俗。在食物方面,他稱羌民吃燕麥、大麥與玉米製的烤餅,以及飲「咂酒」。他並引聖經中的記載,說明古猶代人也吃這種餅,以及飲類似的「酸酒」。在語言方面,由於他無法證明當時羌民的語言與猶太語有何關聯,因此他說羌民「已遺忘了他們的語言,失去了原始卷稿。」在宗教方面,陶倫士所注意的或其所描述的「羌民宗教」,幾乎都與聖經記載或在西亞地區仍然可見的一些宗教習俗相關。因此,他相信在此「蠻荒」之地,土著信仰唯一的最高天神--木比色--就是上帝耶和華。
顯然,陶倫士所說的羌民文化和語言,實為根據他自己選擇性的觀察,加上一些歷史想像而成。他遙想,過去有一典範的羌民文化、語言,一種出於以色列原鄉的典型語言和文化;目前所見的是此典型文化變遷後的殘餘。
1928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黎光明、王元輝
他在調查報告中提到當地的民族有土民、羌民、猼猓子、西番與雜谷民族。對於羌民,報告中記載,「不僅汶川境內有他們的人,在茂縣、理番、石泉、安縣各處,他們的人也不少。」報告中對雜谷人描述較少,只稱「這些人究竟是和汶川的羌民同種嗎,還是和土民同種,我們不敢斷定,我們權當他們是一個獨立的民族,暫給他們一個雜谷民族的名稱。」
他們對羌民的風俗習慣,有如下的綜合描述:
羌民和土民也有很多互為同化的痕跡,有好些風俗習慣是羌、土通有的,究竟不知是誰同化於誰。就衣、食、住三方面的大體言之,羌、土都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說,他找不到「客觀的文化特徵」來區分羌民與土民(由嘉絨藏族地區移來之瓦寺土司屬民)。甚至,對於當前被認為是「羌族」文化標誌的纏頭帕習俗,黎光明等人在報告中特別指出:「以布纏頭代帽,是川西漢人的習慣,並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在他們看來,羌民、土民與漢人至少在服飾文化上差別不大。
(黎光明先生後來離開本所,投入邊區建設工作。1940年代,他任靖化縣縣長。因痛恨黑社會組織「袍哥」在當地種植、販賣鴉片。與川省派駐本地的專員,王元輝,共同設計槍殺當地袍哥首領杜鐵樵。當晚,袍哥即圍攻縣府;次日,縣府被攻下,黎光明先生被亂刀殺死。)
1930至1940年代美籍學者葛維漢(David Crockett Graham)
陶倫士有意忽略各地羌民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建構一個純粹的以色列文化之東方遺存。葛維漢則注意到此文化有相當區域性差異,如原來質樸的羌民服飾在特定地區有各種「加工」(刺繡與花腰帶)。他將此種文化差異歸因於漢與嘉絨兩方面的文化影響。在飲食方面,一方面他強調羌民的日常食物來自於農業生產以及採集、狩獵,以強調其「原始性」;另一方面,他又以使用筷子及部分羌民不吃牛肉的習俗,來強調羌民的漢化。
在羌民的語言方面,同樣的,他指出不同地區的羌語有很大區別。他說,羌民是他曾接觸過的族群(ethnic group)中語言分歧最大的一個。雖然體驗到羌民的語言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仍認為這是一種「語言」;他接受當時中國語言學家聞宥的意見,認為「羌語」是一種古老的藏緬語,因此羌民是黃種人的藏緬語支民族之一。
葛維漢在其著作中,曾感嘆羌民研究的難處。他說:這些人沉默寡言,而又樂於供給一些虛構不實的、他們認為詢問者想要的回答,以及,在語言、風俗習慣上各地羌民又有很大的差別,這都使得研究工作非常困難。
他的感嘆應是由於在他做調查時,有些羌民告訴他,羌民是「以色列人的後裔」,並說他們所信的天神就是「上帝耶和華」。他認為,這是土著受陶倫土及其基督徒羌民助手們教導的結果。葛維漢在他有關羌族的著作中駁斥這種說法,明白指出,羌民並非一神教信徒;除了信他們自己的神外,羌民還信鄰近其他民族的神。
1940年代教育部「大學生暑期邊疆服務團」
調查成員們困惑於「羌民」文化的混雜性。調查者也認為羌人的服飾樸素,並無特色。
羌人服飾,無論男女,並無特別之形式可言。故由服飾觀,無從知其為羌人。衣飾之素淺,與其娛樂之少,同為不解之心理象徵。
以上調查者對於羌人服飾的描述,顯示他們心目中的「羌人文化」十分模糊。他們可以分辨其中那些因素是受「藏人」影響,那些是受「內地」(漢人)影響,但對於羌人服飾,則描述為「素淺」、「無特別形式可言」。關於羌民的音樂歌舞,他們描述為:「其固有音樂僅山歌,而歌謠頗少特具風格,非傳自戎人西番,即來自內地。」至於羌人的語言,調查者也查覺他們的語言複雜、分歧,含有許多外來語;他們稱,有時差別之大,甚至可當作另一系統的語言。但在民族語言範疇等同於民族範疇的概念下,他們認為「羌人之辨別除由語言外,殆無他途可準」。
1940年代 胡鑑民
他努力發掘羌民「固有的」或「傳統的」文化。在服飾方面,他認為羊毛與麻為原料所製的衣服,是羌民傳統的工藝。至於較精緻的繡花鞋與織花帶,他懷疑此是受漢人文化或藏文化影響的產物。在飲食方面,他認為「作饅饅」是羌民的傳統作法。並指出「饅饅入火烤當然是原始的辦法。」由篾籠蒸食,則被他視為「漢化」的結果。
顯然,胡鑑民心目中有相當明顯的「民族進化觀」;羌民是在此進化階梯上較低下的民族。因此所有質樸的、原始的文化因素,都成為羌民的傳統。這見解也表現在他對羌民飲酒習俗的看法上。他說,羌民「像許多淺演民族一樣,嗜酒之癖甚深」。淺演民族,也就是演化較淺的民族。無論如何,對胡鑑民來說,羌人文化探索中充滿了挫折。他承認,「在現在羌民所有的許多工藝與發明之中,要分辨出何者為羌人固有文化,何者由漢化或番化嘉戎化而來,已頗不容易。」
他特別著重羌族的宗教信仰。他說:「羌族的一切文化寶藏--巫術,儀式,歷史,傳說,民族神話與歌舞等等,猶常在巫師與長老領導之下,熱烈的一次一次的表演著。」因此他將之視為羌族文化中最可寶貴的一部分。關於羌族宗教,他駁斥羌民信仰為一神教之說,他認為這是個信鬼神的民族,「其信仰還在靈氣崇拜與拜物的階段」。
華夏邊緣的本質及其變遷
所謂的華夏或中國人此一主體,因主觀建構之邊緣的推移、變遷而成長變化。這也說明了為何在近代國族主義概念下,雖有過一番爭論,最後中國知識份子仍把傳統「四裔」轉變為「少數民族」——「漢族」認同需要異質化邊緣來維持,這一點並未改變。與從前不同的是,在新的「中國」與「中華民族」概念下,如今傳統之「中國」與其「邊緣」合而為一;過去界線模糊的「邊疆」及其外的異族,成為界線明確的之國家「邊界」內的少數民族。漢與非漢間,以及各非漢族群之間,原來模糊、多重而又易變的族群界線,在新學術的民族分類及國家所執行的民族政策下,成為各民族間明確的族群界線。因此可以說,「中華民族」的確是近代的創造,但此創造有其歷史基礎;這是中國傳統與外來思潮的混合產物。中國邊緣的再建構:由蠻夷到少數民族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https://bit.ly/3mrX27l
為什麼外國人總出現在中國重大考古發現的照片里——三星堆被發現
2018-01-23為什麼外國人總出現在中國重大考古發現的照片里——三星堆被發現 - 愛經驗 https://bit.ly/3cW2n3v
早在1929三星隊宛如外星人留下的的陪葬品驚險中國,再到86年祭祀坑的現身,大量稀奇古怪的文物出土,三星堆的發掘與考古活動已經有了八十多年。這10多平方公里的面積內,發掘出了5000年左右的古蜀國文明。它見證了中國一向以黃河文明為中華歷史起點的敘述,向更遠的西部延伸。
三星堆遺址出的文物越多,大家的疑惑就越大,最早的發現者之中總是有西方人的面孔,他們是有多愛在中國挖寶貝啊。就是下面這張照片
1934年三星堆發掘現場的合影,左一為林名均,右一為葛維漢。
葛維漢於1884年3月21日出生在美國阿肯色州的格林福林斯特。1931年,葛維漢被任命為美國國家博物館合作者並再次受聘於四川省省會成都的美國浸禮教會差會。從1932年至1948年退休,葛維漢一直在成都華西協合大學教授文化人類學和考古學。他還被任命為該大學考古、藝術和人類學博物館館長。其實這些外國人一般都是其母國留在中國的文物探子
難道是外星人創造了三星堆文明?
圍繞三星堆世界各國的考古專家爭論了幾十年,很多問題至今都沒有破譯,甚至猜測稱三星堆遺址是來自「外星人」的文化。
1934年三星堆發掘現場
三星堆的發掘簡直給我們創造了跨越時空的迷宮
1986年發掘現場
廣漢玉器
其實86年發現的祭祀坑是三星堆考古進程中重要突破。都是在當地農民勞動中被發現的
發現人燕道誠(中)和他兒子燕青保(右)
燕道誠在成都的古玩市場上出售了部分挖出來的玉器。古董商們都來找他了,後來他又賣了不少
1929年出土存放在燕家院土磚牆側的大玉、石璧
幾年時間越買越少,但是廣漢出了玉器的事情很快傳遍成都吸引來了考古學家。
1931年春廣漢傳教英國神父董篤宜,從燕道誠手中得到了幾件玉石器。你沒看錯,這些教會的人就開始便宜買貨了。華西協和大學的美籍歷史學家戴謙和當時鑒定這些玉器為商周遺物。幾年後,當戴謙和把這些玉器放到他的好朋友葛維漢面前時,葛維漢驚愕不已。
葛維漢也是美國人,早在1911年就作為傳教士到了四川,是個中國通。後來他返回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了宗教學博士學位,繼而又在哈佛大學學習了考古學、人類學。1932年,葛維漢重返中國,在華西協和大學任博物館館長、兼任人類學教授,教考古學、文化人類學。
葛維漢
1934葛維漢來到燕家,他們先在燕家的房屋旁邊進行開方試掘,共發掘出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六百餘件,比燕家人第一次挖出的還要多。
一號祭祀坑俯拍圖
葛維漢的考古報告震動了歷史學界,掀起了一股「廣漢文化」的研究熱潮。就連當時身在日本的郭沫若也跑回來看。郭沫若當時正潛心研究流落日本的中國甲骨文,已是甲骨文大家。
一號祭祀坑出土的金杖
一號祭祀坑出土文物全貌,看起來有些亂,清理好了件件頂級
新中中國成立了
二號祭祀坑出土青銅縱目面具現場
1955年,馮漢驥派學生王家佑到廣漢展開廣泛的田野調查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復人員楊曉鄔修復青銅神樹
殘斷的大立人像
之前黃河流域一直被認為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我們稱黃河為「母親河」,史學界的主流看法是中國文明一元起源論,黃河流域的夏、商文化是中華文明的唯一起源地,中國的其他文明只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傳播,或其分支。但是三星堆證明這裡也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1963年再次進行田野考古,最後總結為:「這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只要再將工作做下去,這個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現於我們的面前。」後來事實真的如此
二號祭祀坑出土大立人像現場
磚廠取土堆
1979三星堆旁建起了一座磚廠。被考古工作者視為重要遺迹的三星堆,卻被磚廠當成了三個最便捷的天然大土堆,正源源不斷地取土燒磚呢。三星堆屬於中興公社範圍。公社就利用三星堆的土堆取土,辦了個集體磚廠。挖出的陶片被成堆扔在一邊。我一看,陶片年代應該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火候不高,手感比較軟,器形也比較原始,說明時間很古老。」
二號祭祀坑出土青銅器
在這裡村民偶爾挖到些玉石製品樣子並不讓人覺得珍貴。1978年,敖天照聽說有人幾年前發現了一坑顏色漂亮的「鵝卵石」,已經散落各家。他走村串戶去收集,「一看就是人工打磨過的磨石」。村民們把「石頭」留在家裡「給娃娃耍」,聽說有文物價值,也相當配合地上交了。村裡一位大媽聽到了說,「我家有一個磨過口的石片,還很好用」。敖天照到她家一看,「是一把十幾厘米的石斧」。他給大媽拍了照片,獎勵她1塊錢。用很少的錢,作為上交文物的獎勵給了老鄉。他把收集來的上百件文物,暫時存放在廣漢縣房湖公園內一處閑置的空房子里,他自己也居住在附近。為什麼外國人總出現在中國重大考古發現的照片里——三星堆被發現 - 愛經驗 https://bit.ly/3cW2n3v













三星堆首次考古發掘人葛維漢
編輯:zhujy發佈時間:2021-03-23
葛維漢,美國人,1884年3月出生於阿肯色州。 1920年獲芝加哥大學宗教心理學碩士學位,1927年獲該校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
1911年,他以美國浸理會牧師身份來到中國,1913年抵川,直到1948年返國。 其間除短期回國述職和進修外,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多年,大部分時間是在四川度過。 回國后,定居於科羅拉多州,繼續利用自己在中國搜集的豐富材料進行研究,發表了多本與中國西南民族與宗教相關的專著,先後獲得了兩個古更赫姆獎(Guggenheims)和一個維京獎(Viking)。 曾任美國文化人類學會會員、美國民俗學會會員、遠東研究所成員和皇家地理學會成員,以及美國紐約動物學會終身會員。
1932年,美國哈佛燕京學社鑒於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之重要,派葛維漢博士來成都接任館長,同時擔任華西協合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 在此期間,他曾十三次赴四川的藏族、彝族、苗族、羌族地區進行調查研究,對當地少數民族文物進行了系統收集,整理。 所得資料,至今仍為研究西南少數民族文化所必備。
1933年冬,他與林名均一起主持了廣漢三星堆的首次考古發掘,揭開了"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序幕。 他還主持和參加了對四川部分漢墓、唐宋邛窯、琉璃廠窯的發掘,正確記錄了出土文物,撰寫發掘報告。 在他的主持下,華西大學博物館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在擔任館長期間,葛維漢發表與西南民族、宗教,華大博物館相關論文近百篇,其中55餘篇刊載於《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上,其漢州(廣漢)遺址,漢墓及唐宋窯址之發掘報告,實為四川考古學開一新紀元。 其對於西南地區邊疆民族之研究成績,對近代人類學亦頗多貢獻。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秘書長、華大博物館館長葛維漢也意識到了這片遺址的重要性,他以廣漢遺物之富於考古價值的因素,詢問董氏目前發現的詳細情況,併萌發了對此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的念頭,董氏也同意幫其聯絡相關人士,疏通關係。
就在當年冬天,葛維漢獲得了廣漢縣政府的批准以及四川省政府和四川教育廳的發掘護照。
次年三月,葛維漢接受了廣漢縣長羅雨蒼的邀請,前去主持廣漢遺址首次科學考古發掘。 但當時的社會情況較為特殊,據學會的國人學者林明鈞說:「以西人主持其事,在蜀尚屬創舉,恐引來不必要之誤會與糾紛。 ”。
鑒於照顧當時國人民族情緒的因素,葛維漢與林明鈞組成的華大博物館科學考古隊只負責挖掘工作,其它的統由羅縣長出面主辦,當時葛維漢也自詡"我們只是縣長的科學指導者"。
葛維漢教授(右一)及部分協助發掘的當地鄉紳合影
1934年3月16日,科考隊對廣漢燕家住宅旁發現玉器的小溪與田壩進行了考古發掘。 但由於當時社會治安不好,土匪出沒現象嚴重,為防止發生不測之事,發掘10日便宣告結束。
這次發掘,出土的玉、石、陶器共有600餘件,羅縣長認為這些文物很有科學價值,就代表縣政府捐贈給了華大博物館收藏和研究。 而這次對廣漢遺址的首次科學考古發掘,也開啟了"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序幕。
1935年,葛維漢在《學會雜誌》第6卷上發表《漢州發掘簡報》,為三星堆文化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也是早期研究廣漢遺址遺物的集大成者。
這份簡報在當時而言可謂異常完備,其將董氏發現廣漢遺物經過的過程、戴氏對廣漢出土玉石器的研究都詳細記錄;同時還將近現代考古分析手段對於三星堆遺址的應用也做了充分記錄 華西協合大學化學家科利爾博士對廣漢出土陶片進行的化學分析,成都加拿大學校校長兼美術家的黃思禮運用《勃雷德萊標準色素圖》對廣漢出土的文物進行色彩鑒定 ;甚至就連郭沫若1934年7月給林明鈞的信,也有所收錄。
相關人士運用具有現代意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廣漢遺物進行開拓性研究,對後來的學者啟迪很大,郭沫若稱他們是「華西科學考古工作的開拓者」。 此後,國人也陸續發表了一些三星堆研究的成果作品。葛维汉是谁为什么发掘三星堆_三星堆首次考古发掘人葛维汉_我爱历史网 https://bit.ly/3wBtEQw
-----------------------
三星堆首次考古發掘人葛維漢
編輯:zhujy發佈時間:2021-03-23
葛維漢,美國人,1884年3月出生於阿肯色州。 1920年獲芝加哥大學宗教心理學碩士學位,1927年獲該校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
1911年,他以美國浸理會牧師身份來到中國,1913年抵川,直到1948年返國。 其間除短期回國述職和進修外,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多年,大部分時間是在四川度過。 回國后,定居於科羅拉多州,繼續利用自己在中國搜集的豐富材料進行研究,發表了多本與中國西南民族與宗教相關的專著,先後獲得了兩個古更赫姆獎(Guggenheims)和一個維京獎(Viking)。 曾任美國文化人類學會會員、美國民俗學會會員、遠東研究所成員和皇家地理學會成員,以及美國紐約動物學會終身會員。
1932年,美國哈佛燕京學社鑒於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之重要,派葛維漢博士來成都接任館長,同時擔任華西協合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 在此期間,他曾十三次赴四川的藏族、彝族、苗族、羌族地區進行調查研究,對當地少數民族文物進行了系統收集,整理。 所得資料,至今仍為研究西南少數民族文化所必備。
1933年冬,他與林名均一起主持了廣漢三星堆的首次考古發掘,揭開了"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序幕。 他還主持和參加了對四川部分漢墓、唐宋邛窯、琉璃廠窯的發掘,正確記錄了出土文物,撰寫發掘報告。 在他的主持下,華西大學博物館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在擔任館長期間,葛維漢發表與西南民族、宗教,華大博物館相關論文近百篇,其中55餘篇刊載於《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上,其漢州(廣漢)遺址,漢墓及唐宋窯址之發掘報告,實為四川考古學開一新紀元。 其對於西南地區邊疆民族之研究成績,對近代人類學亦頗多貢獻。
華西邊疆研究學會秘書長、華大博物館館長葛維漢也意識到了這片遺址的重要性,他以廣漢遺物之富於考古價值的因素,詢問董氏目前發現的詳細情況,併萌發了對此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的念頭,董氏也同意幫其聯絡相關人士,疏通關係。
就在當年冬天,葛維漢獲得了廣漢縣政府的批准以及四川省政府和四川教育廳的發掘護照。
次年三月,葛維漢接受了廣漢縣長羅雨蒼的邀請,前去主持廣漢遺址首次科學考古發掘。 但當時的社會情況較為特殊,據學會的國人學者林明鈞說:「以西人主持其事,在蜀尚屬創舉,恐引來不必要之誤會與糾紛。 ”。
鑒於照顧當時國人民族情緒的因素,葛維漢與林明鈞組成的華大博物館科學考古隊只負責挖掘工作,其它的統由羅縣長出面主辦,當時葛維漢也自詡"我們只是縣長的科學指導者"。
葛維漢教授(右一)及部分協助發掘的當地鄉紳合影
1934年3月16日,科考隊對廣漢燕家住宅旁發現玉器的小溪與田壩進行了考古發掘。 但由於當時社會治安不好,土匪出沒現象嚴重,為防止發生不測之事,發掘10日便宣告結束。
這次發掘,出土的玉、石、陶器共有600餘件,羅縣長認為這些文物很有科學價值,就代表縣政府捐贈給了華大博物館收藏和研究。 而這次對廣漢遺址的首次科學考古發掘,也開啟了"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序幕。
1935年,葛維漢在《學會雜誌》第6卷上發表《漢州發掘簡報》,為三星堆文化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也是早期研究廣漢遺址遺物的集大成者。
這份簡報在當時而言可謂異常完備,其將董氏發現廣漢遺物經過的過程、戴氏對廣漢出土玉石器的研究都詳細記錄;同時還將近現代考古分析手段對於三星堆遺址的應用也做了充分記錄 華西協合大學化學家科利爾博士對廣漢出土陶片進行的化學分析,成都加拿大學校校長兼美術家的黃思禮運用《勃雷德萊標準色素圖》對廣漢出土的文物進行色彩鑒定 ;甚至就連郭沫若1934年7月給林明鈞的信,也有所收錄。
相關人士運用具有現代意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廣漢遺物進行開拓性研究,對後來的學者啟迪很大,郭沫若稱他們是「華西科學考古工作的開拓者」。 此後,國人也陸續發表了一些三星堆研究的成果作品。葛维汉是谁为什么发掘三星堆_三星堆首次考古发掘人葛维汉_我爱历史网 https://bit.ly/3wBtEQw

---------------------------------

語言文化---多元的聲音 多元的樣貌 羌曆年
語言
在羌族地區最常聽見的共同語言﹐是一種漢語川西方言--他們稱之為「漢話」。
另外有一種本土語言﹐本地人稱為「鄉談話」。
由於各地口音差別很大﹐因此「鄉談話」只能通行於很小範圍的人群內──通常是一條溝之中。
西路與北路各溝羌族﹐許多人都能說鄉談話與漢話。
岷江東路各村寨羌族﹐幾乎都只能說漢話﹐特別是中年以下的人。
北川地區大部分的羌族﹐在他們祖父那一代說的便都是漢話了。
住在城鎮中的羌族﹐一般都說漢話;
知識分子還能說普通話(北京話)。
只有離公路較遠的深溝高山村寨﹐才是全然說鄉談話的地區。
所謂「鄉談話」﹐也就是語言學家所稱的「羌語」﹔
分南部方言與北部方言﹐又各分為五個地方土語。
事實上﹐在同一土語群中的人們﹐彼此也不一定能用鄉談話溝通。
正如一位羌族朋友所說的:「我們的話走不遠;一條溝有一條溝的話﹐有時同一溝中陰山面與陽山面的人說話都不一樣。」
正因為以鄉談話溝通有困難﹐所以各地羌族在一起時﹐說的都是漢話。
東路羌族經常自豪於他們能說很好的漢話﹐並嘲笑西方﹑北方及深溝中羌族或藏族所說的漢話。
甚至他們認為自己的漢話是「不須要學就會」﹐而鄉談話卻要學才會。
相反的﹐西路與北路的羌族雖然說起漢話來口音重﹐但有些男人卻能說一些鄰近的藏族方言。
譬如﹐有些松潘埃期溝羌族能說一口熱務藏語;
許多理縣羌族也會說嘉絨藏語。
除了地域性語言差別外﹐男﹑女的語言使用也有不同。
與女人相比﹐通常男人的漢話(或藏話)說得要好得多。
據他們說﹐這是因為女人不常接觸外界﹐所以其它語言說不好。
即使在鄉談話上﹐他(她)們也認為男人的辭彙多而靈活﹐女人的語言則保守而較具地方特色。
所謂男子的羌語辭彙多而靈活﹐顯然是因為他們用了許多漢語﹑藏語與鄰近羌族方言的借詞。
除此之外﹐同一村寨上下世代人群間的語言也有些差別。
許多老年人用的詞彙﹐現在已完全不用了﹔
保留「古語」較多的羌族端公唱詞﹐目前絕大多數的本地羌族人都聽不懂。
對於羌族民眾而言﹐在羌族認同上最大的困惑可能是語言上的問題。
過去他們對「爾瑪」的定義﹐常是「說我們同樣這一口話的人」。
如今「爾瑪」被擴大理解為「羌族」﹐然而卻包括了許多彼此不能通話的人群。
羌族民眾對此的解釋是﹐人住得分隔(因為被打散了)﹐語言就慢慢變了。
他們也常在交談中﹐努力嘗試了解其它地區羌族所說的「鄉談話」。
但羌族知識分子並不滿足於此。
1989 年起﹐在四川省民族委員會的羌族幹部主持下﹐一項羌族語文創制與推廣計劃開始進行。
經過討論與研究﹐決定以「曲谷方言」為標準羌語﹐以此制定拉丁拼音的羌族文字﹐並編輯相關的《羌語詞典》。
為了推廣標準化的羌語文﹐汶川的威州師範學校建立「羌文班」﹐培訓標準羌語文師資。
同時在羌語文的創制過程中﹐羌族知識分子也致力於羌族文化的蒐集﹑研究與推廣。
雖然如此﹐推行標準化的羌語顯然不易。
2002年威州師範學校的羌文班已停止招生。
主要原因應是﹐在本地普遍以「漢話」(川西方言)作為各地人群間的「共同語」至少已有百年歷史﹐而由於各村寨﹑各溝的認同與區分機制﹐也讓他們不易改變原有的「鄉談話」。
況且各溝各寨羌族與外界接觸日多之後﹐使用「漢話」的機會更普遍﹐因而「鄉談話」仍在繼續流失之中。
共同本土語言文字的推廣﹑使用雖然缺乏成效﹐但這些活動作為一種社會記憶展演﹐推廣了共同羌語此一觀念﹐在凝聚羌族認同上仍有相當意義。
羌曆年
「羌曆年」是否為羌族傳統的「新年」﹐在當今羌族中有些爭議。
在陶倫士與胡鑑民的著作中﹐都曾提及羌民的新年是在陰曆十月初一﹔
主要活動是殺牛羊還願。
然而在葛維漢的書中﹐他以汶川﹑理縣之間的和平寨﹑穆山寨等地習俗為例指出﹐
「還願」或在六月初一﹐或八月初一﹐或十月初一﹐各寨間沒有統一的日期。
而且﹐他並未將此節日視為羌民的年節。
《川西調查記》中所載的羌民歲時節日﹐有過年﹑清明﹑端午﹑中秋等﹔
本地人「過年」與漢人習俗相同﹐是在陰曆正月。
陶倫士與胡鑑民所描述的是汶川與理縣東部的「羌民」。
所謂羌曆年在這些地區原稱作「牛王會」﹐或與漢人年節「冬至」相混﹐因此也稱作「過小年」。
「牛王會」或拜牛王菩薩的習俗﹐在各地有不同的舉行時間﹐有不同的儀式﹐甚至有不同的節慶意義。
在農業較重的汶川和理縣東部地區﹐這相當於一種答謝神恩(還願)的秋收節。
然而在茂縣西路牧業遠較汶﹑理地區為重的赤不蘇﹐只有養牛羊較多的家庭祭牛王菩薩。
也就是說﹐愈往北路與西路去﹐「牛王會」的節日意義就愈淡化﹐或根本沒有。
無論是冬至過小年﹐或是牛王會﹐顯然都是與漢人民間信仰相關的習俗﹐它們的流行程度﹐也與本地人的漢化程度相對應。
事實上﹐無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或是今日﹐在所有當前羌族地區中﹐一年最重要的節日便是過大年﹔與漢族一樣的過陰曆年。
過年時﹐吃年夜飯﹑祭祖﹑舞龍舞獅等等﹐也與漢族大體相同。
更重要的是﹐在「羌語」中根本沒有「月分」與「一年起始」的概念﹐自然也沒有所謂的「羌曆年」了。
無論如何﹐「過大年」被認為是漢人習俗﹐因此在羌族文化建構中「牛王會」逐漸成了「羌曆年」。
地方自治政府在推行「羌曆年」上扮演了主要角色。
1988 年茂縣舉辦全羌族的「羌曆年」慶祝活動。
次年﹐在汶川縣舉辦慶典﹐1990 年由理縣舉辦﹐1991 年由北川縣舉辦。
「羌曆年」成為羌族新年的詳細過程並不清楚。
胡鑑民等人對羌民「過年」習俗的描述﹐可能有一定的影響。
各地羌族民眾大多明白﹐過去並沒有「羌曆年」的習俗﹔他們常將之歸於某一重要「羌族」的鼓吹或推動。
如一位北川青片鄉的羌族老人所言﹕
現在這十月初一﹐在理縣那幾個寨子調查的﹐而且他們也叫過小年﹐不知為何弄成羌曆年。現在茂縣的人還問﹐怎麼把個十月初一變成羌曆年。
我說﹐我還要問你們呢。八七年在成都的那些羌族﹐何玉龍﹐一個老紅軍﹐每一縣派一些人去跟他們過羌年十月初一﹐後來就成了傳統了。
八八年在茂縣﹐八九年在汶川﹐九十年在理縣﹐九一年在北川。
就這樣形成了。現在老百姓對這也反感。他們認為不是十月初一。
松潘小姓溝的一位羌族﹐對此有另一種詮釋﹐他說﹕
解放後﹐還有日本人的頭頭來﹐他說羌族是日本人的舅舅﹐說羌族怎麼沒見了。
所以後來茂汶就弄一個羌族自治州說﹐就有了羌曆年﹔就是日本人問的。
羌曆年是好多號?這是後來才成立的﹐成立了三年﹑四年了吧﹐跳舞﹑唱歌﹑咂黃酒。
在許多羌族的記憶中﹐羌曆年不僅不是一項舊傳統﹐相反的﹐在他們的言談中常出現「開始過羌曆年的時候」這一時間座標。
這個時間起點座標﹐代表一個新的開始--較好的經濟生活﹐較多的觀光客﹐經常舉辦的羌族歌舞表演。
跳鍋庄
羌曆年慶典中﹐最重要的活動便是「跳鍋庄」表演。「跳鍋庄」﹐又稱「沙朗」﹐是一種團體歌舞﹐目前被認為是阿壩州藏﹑羌族共有的一種地方文化。
但許多地方民眾都說﹐當地過去沒有這傳統﹐這是近年來年輕人由外面學回來的。
在茂縣牛尾巴的新年慶典中﹐當年輕人跳「鍋庄」時﹐老年人聚在一起跳「尼薩」(聯﹕一段尼薩文)--據稱﹐這是本地過去的傳統歌舞。牛尾巴的一位老年人說﹕
鍋庄有﹐以前我們跳的是尼薩﹐尼薩日北﹐就是不跳腳﹐只是轉圈圈。
你唱一段﹐我唱一段﹐像對詩一樣﹐跳舞根據跳那個。解放過後﹐他們參加工作的帶回來的(鍋庄)﹔
以前不興跳﹐不會。
沙朗的歌詞﹐鍋庄的意思不曉得﹐尼薩的意思知道。
沙朗原來不是羌族舞﹐只是現在進化了﹐一些文人吧﹐編出來的。
尼薩有﹐過年有過年的內容﹐全部是羌族語言來對的(按: 來唱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它地區﹐幾乎也沒有任何羌族民眾知道「鍋庄」的歌詞內容。
「鍋庄」似乎是由西方(目前的嘉絨地區與黑水地區)傳來的歌舞﹔
過去愈往東邊﹐此種傳統愈弱或根本沒有。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調查者已指出當時羌民的鍋庄歌舞並不普遍﹐有此習俗的只是緊靠著「西番」或嘉絨藏族的羌民。
目前在有此傳統的羌族地區﹐據老年人說﹐過去一地有一地的鍋庄﹐皆有不同之處。
自稱「爾勒瑪」的黑水藏族﹐有些老人也說﹐過去他們跳兩種沙朗--「赤部沙朗」與「爾勒瑪沙朗」﹔
前者指的是由上游地區傳來的沙朗﹐後者是「我們的沙朗」。
而這些老人所稱的「爾勒瑪」﹐也只是指一小區域人群。
自 1989 年以來﹐在阿壩州政府與其下各縣政府的倡導下﹐典型的羌族鍋庄與藏族鍋庄分別被編成幾套﹐並推廣到各地民眾之間。
各縣城的少數民族知識分子﹐是熱心的推廣者。
如今鍋庄歌舞經常在羌族地區各種公私慶宴如婚禮﹑運動會或羌曆年中表演﹐成為當地旅遊活動的重要展演項目﹐也成為羌族年輕男女日常農閒時的娛樂。
如今對羌族而言﹐它不僅是本民族文化象徵﹐也是阿壩州包括藏﹑羌的少數民族文化與團結的象徵。
羌族婦女服飾
羌族婦女多有包頭帕的習俗﹐各地有不同的包纏法。
最大的差別是「搭帕子」與「包帕子」的區分﹔
前者流行在鄰近嘉絨或黑水藏族的羌區﹐如赤不蘇與理縣﹐後者流行在其它羌族地區。
包帕子的方式﹐在三龍溝﹑黑虎溝﹑蒲溪溝﹑永和溝等地都有相當差別。
甚至在一個溝中﹐相鄰村寨間都有細微的區分。
鞋子﹑領裌與圍腰上的繡花﹐也被視為當前羌族傳統服飾重要特色。
西路與北路羌族的繡花﹐以幾何圖案的「十字繡」為多﹐東路則流行以花朵圖案為主的「刺繡」。
無論如何﹐目前穿著這色彩豔麗而又多變化的「傳統羌族服飾」的人﹐幾乎都是村寨中的婦女。
這些服飾特徵中有那些是「傳統的」﹐至少是從二十世紀上半葉沿續而來的傳統?
在二十世紀前半葉﹐陶倫士﹑葛維漢﹑胡鑑民與《川西調查記》的作者們所描述的「羌民」服飾﹐經常是形式素樸﹑色彩單調(像)(像)。
或認為﹐無法由服飾來辨別誰是羌族。葛維漢與胡鑑民都曾注意到﹐在衣鞋上繡花的習俗﹐在較漢化或藏化(嘉絨化)的地區比較流行﹐因此他們懷疑羌民是由鄰近漢族或嘉絨藏族那兒習得繡花習俗。
此外﹐在 1928 年﹐調查者黎光明已見到汶川羌民有纏頭巾的習俗。
但他指出﹐「以纏頭代帽是川西漢人的習慣﹐並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
1934年中國旅行家庄學本描述汶川羌民的服飾時﹐也認為「此地的漢羌和山外的川人同樣纏著素淨的白頭帕」。
顯然不同於過去的素樸﹐現代羌族村寨婦女服飾在色彩上非常炫麗﹐衣裙上的圖案多而複雜。
其次﹐當近幾十年來婦女服飾逐步特殊化而表現民族與地域特色時﹐相反的﹐無論在村寨或在城鎮中﹐羌族男人服飾卻朝中性化﹑一般化與現代化發展。
由服飾上我們看不出各地羌族男子有何不同﹐也看不出羌族男子與漢人有何差別。
至於羌族婦女服飾上的地域性差異﹐這倒是由葛維漢﹑胡鑑民的描述中﹐直到今日各地羌族婦女的穿著上﹐始終如一的現象。
在現代「民族」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概念中有兩大因素︰團結(民族化)與進步(現代化)。
除了以共同「起源」團結﹑凝聚民族成員之外﹐還強調或追求該民族的「進步」與「現代化」。
此種二元特性﹐使得人們對「民族傳統文化」有兩種相矛盾的態度﹔
一方面「傳統文化」促成民族團結因此值得強調﹑推廣﹐
另一方面「傳統文化」又代表落後而須被改革或迴避。
由於對「傳統」的愛憎﹐以及民族內部的核心與邊緣區分﹐
於是以中華民族而言﹐漢族不願穿著「傳統民族服飾」﹐而自豪於少數民族皆穿著「傳統民族服飾」﹐此隱喻著漢族的現代化﹐與少數民族的落後。
在羌族之中﹐城鎮羌族知識分子本身不穿「傳統民族服飾」﹐但他們自豪於村寨中的羌族仍穿著本民族服飾。
同時﹐羌族城鎮居民也認為自身較現代化﹑較進步﹐而鄉下人要保守﹑落伍些。
在羌族村寨中﹐男性也不穿本民族傳統服飾﹐但他們自傲於「本地女人都還穿本民族傳統服飾」。
村寨中的男人也認為﹐男人見的世面較多﹑較進步﹐女人較封閉﹑保守。
於是﹐羌族村寨女性在強化各種社會區分的核心與邊緣權力關係下﹐成為「傳統」的承載者。
祭山會與廟會
祭山會活動﹐在部分羌族村寨中是一種中斷而難恢復的傳統﹐另一些村寨則一直維持此宗教活動。
一般來說﹐愈遠離城鎮與交通幹線的村寨﹐愈容易或愈有必要維持此傳統祭山活動。
因此以整個羌族地區而言﹐西方﹑北方的深山村寨民眾較重視祭山會活動。
祭山神的傳統是﹐即使在同一溝中各寨都是各祭各的山神﹐各寨祭山日期與儀式過程也不同。鄰近的嘉絨與黑水藏族亦如此。這也反映﹐「祭山神菩薩」是一種本地的村寨傳統﹐而不只是一種羌族傳統。
近年來﹐在本土與外來羌族文化研究者的鼓勵與安排下﹐以及在恢復羌族文化及發展觀光的動機下﹐有些村寨曾盛大舉行祭山活動。
在這些活動中﹐常吸引大量觀光客﹑記者﹑學者與鄰近居民參與。
介紹這些羌族祭山活動的文字與圖象﹐透過各種媒體傳播﹔
尤其出現在羌族知識分子編輯出版的有關羌族文化的書刊中﹐更增強了祭山神(或祭神樹林)為羌族代表性宗教活動此一意象。
在過去﹐絕大多數羌族地區都曾流行「廟會」活動。
在許多較漢化的羌族地區﹐「廟子」替代山神﹐也承繼了山神維持各村寨資源界線的意義。
因此﹐在 1980 年代中期以來﹐許多村寨也嘗試重建文革時期被打爛的「廟子」﹐恢復廟會活動。
但這些東嶽廟﹑觀音廟﹑川主廟卻無「少數民族宗教文化」此一護身符﹐因此難免被視為「封建宗教迷信」而遭受部分民眾的質疑﹐也受當地政府的壓抑。羌~語言文化---多元的聲音 多元的樣貌 羌曆年~我們這個民族 歷史社會與文化 @ 東方明珠~中華文明 :: 隨意窩 Xuite日誌 https://bit.ly/3fPw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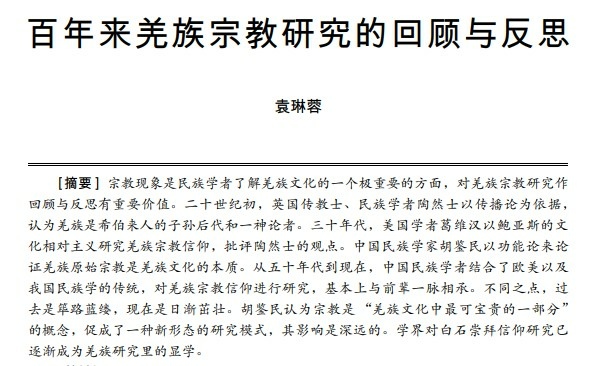

胡鑑民介紹
【生卒】:1896—1966
江蘇宜興人,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生。 中學畢業後,於1921年赴新加坡,在《新中華日報》社任編輯。 1922年秋,入法國斯太斯堡大學攻讀社會學,獲碩士學位。 參加中國留法同學會。 後赴比利時、德國繼續研究社會學。 1931年春回國,在上海與人共同創辦上海勞動大學;同年下半年,任國立中央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1936年夏,任國立四川大學教育系教授,並參加中國社會學會。 1953年後,歷任四川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歷史系教授、系主任。 1966年病逝。 終年70歲。 著有《中國社會的分析》、《羌族之信仰與習為》、《羌民的經濟活動型式》、《苗人的家庭與婚姻習俗瑣記》等。
摘要: 胡鑒民是中國早期政治社會學教學和研究的代表。他將20世紀西方政治社會學引入中國,并運用西方政治社會學相關的理論與方法從事對自然生產的政治社會、政治起源與變遷、政治組織與民族政治文化變遷等的研究,力圖實現政治社會學的中國化,同時又注重建立早期中國政治社會學的理論框架、學科體系等,從而開創了中國政治社會學的學術研究傳統。
-----------
胡鑑民(1896-1966) 江蘇省宜興市太華鎮人,社會學家、民族學家、歷史學家。
他幼年讀四書五經,後入國山高等小學。畢業考入上海哈同中學免費生。因家庭經濟困難,畢業後未能繼續升學。1921年,經姐夫、友人的介紹和資助,到新加坡,在華僑舉辦的《新中華日報》社任編輯,1年後,赴法國勤工儉學。後考入法國里昂斯坦斯堡大學,攻讀社會學,心理學等,獲社會學博士學位。後又赴德國、比利時等地繼續研究社會學,於1931年春回國。
胡鑑民從海外歸來後,與幾位留法同學共同創辦“上海勞動大學”,遭國民黨勒令停辦。經人介紹, 1931年下半年受聘於中央大學,任社會學課教授。1936年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聘任教育學系教授。主講社會學、心理學等課程。1942年,四川大學從峨嵋遷回成都,其時,他除在川大上課外,還在內遷成都的金陵大學、齊魯大學兼課。
歷史教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四川大學軍管會任命為文學院代理院長兼歷史系主任。1953年後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1954年後,因身體多病,辭去行政職務,專任歷史系教授。1958年,任學校五洲史教研室主任。
受涂爾干學派影響,他是中國社會學界中重視心理學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的學者。1937年自費到汶川、理縣等地進行社會實地調查,寫出有關羌族社會生活和習俗的論文。在社會學方面的代表性論著主要有:《中國社會的分析》《觀念社會學》《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社會現象的研究》《關於社會學幾個根本問題的討論》《社會學與社會問題研究》《印度喀拉拉邦的昨天和今天》等。在民族學方面的代表性論著主要有:《羌族的信仰與習俗》《羌民的經濟活動形式》和《苗人家族與婚姻習俗瑣記》等。其主要史學論文有《西周社會性質問題》等。
1966年1月30日,胡鑑民在成都逝世,終年69歲。
【人物春秋】胡鑑民——歷史學家_成都方誌 - 微文庫 https://bit.ly/31Q6Uhx
宗教現像是民族學者瞭解羌族文化的一個極重要的方面,對羌族宗教研究作回顧與反思有重要價值。 二十世紀初,英國傳教士、民族學者陶然士以傳播論為依據,認為羌族是希伯來人的子孫後代和一神論者。 三十年代,美國學者葛維漢以鮑亞斯的文化相對主義研究羌族宗教信仰,批評陶然士的觀點。 中國民族學家胡鑒民以功能論來論證羌族原始宗教是羌族文化的本質。 從五十年代到現在,中國民族學者結合了歐美以及我國民族學的傳統,對羌族宗教信仰進行研究,基本上與前輩一脈相承。 不同之點,過去是篳路藍縷,現在是日漸茁壯。 胡鑒民認為宗教是"羌族文化中最可寶貴的一部分"的概念,促成了一種新形態的研究模式,其影響是深遠的。 學界對白石崇拜信仰研究已逐漸成為羌族研究里的顯學。
--------------------
胡昭曦
胡昭曦
出生 1933年2月
中國四川省自貢市
逝世 2019年11月3日(86歲)
中國四川省成都市
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職業 歷史學家
政黨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學術背景
母校 四川大學
胡昭曦(1933年2月-2019年11月3日),齋名旭水齋,四川自貢人,中國史學家,主要研究宋史與巴蜀歷史。
生平
1933年2月出生於四川省自貢市,1949年8月在自貢市旭川中學參加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合會,後任教導幹事;1956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師從徐中舒、蒙文通、繆鉞、馮漢驥、胡鑒民、蒙思明、盧劍波等著名學者。大學畢業後,胡昭曦留校擔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助教。
1983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7年升任教授,1993年被批准為博士生導師;1992年成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2003年5月離職休養。
2019年11月3日12時15分,在華西醫院逝世[1]。
學術作品
胡昭曦在大學時先後撰寫《論漢晉的氐羌和隋唐以後的羌族》、《關於評價王安石變法的幾個問題》、《熙豐變法經濟措施之再評價》等文,得到了學界的肯定。
在晚宋史特別是宋蒙(元)關係史研究方面,胡昭曦有著重要貢獻。由於資料零散,晚宋史一直是宋史研究的薄弱環節。胡昭曦迎難而上,完成《宋末四川戰爭史料選編》(合著)、《宋蒙(元)關係研究》、《宋蒙(元)關係史》、《宋理宗宋度宗》(合著)等專著,對宋理宗宋度宗時期的政治、宋蒙關係、晚宋史分期等問題作了深入研究。
胡昭曦將宋史文獻資料與川渝地區的歷史遺蹟考察相結合來進行研究。他走訪了四川省內50多個市、縣及相關地區,收集大量實地調查材料,先後出版《王小波李順起義考述》《張獻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廣填四川」》《四川古史考察札記》《四川古代史稿(宋元部分)》《四川書院史》等專著和《巴蜀歷史文化論集》等論文集。
胡昭曦於2003年離休,離休後先後發表60餘篇學術論文,匯集出版《宋代蜀學論集》、《巴蜀歷史考察研究》、《旭水齋存稿》、《旭水齋存稿續集》等多部專著。胡昭曦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bit.ly/2OwhwPQ
三星堆遺址 入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2021-11-03 00:00 聯合報 / 大陸特派員王玉燕/綜合報導
今年9月,在三星堆考古發掘現場8號「祭祀坑」內發掘的青銅神獸。(新華社)
三星堆遺址 入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 大陸傳真 | 兩岸 | 聯合新聞網 https://bit.ly/3kbn92o
在日前舉行的大陸第三屆考古學大會開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名單,位於四川省德陽市的三星堆遺址等100項發現入選。
2021年是大陸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經過幾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考古工作取得了累累碩果。此次舉行的「百年百大考古發現」遴選推介活動於今年5月啟動,經過各地文物主管部門審核、專家提名,最終確定321項發現作為候選項目,並從中選出百大考古發現。
三星堆遺址發現於上世紀20年代末,是迄今大陸西南地區發現分布範圍最廣、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古文化遺址,其文化堆積距今約4500-2800年,面積達12平方公里;核心區域面積約3.6平方公里,為古蜀國都城遺址,年代約當商代。
1986年,三星堆1號、2號「祭祀坑」,出土青銅大立人像、青銅神樹、青銅面具、金面罩、金杖、象牙等上千件珍貴文物,「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其年代為商代晚期(距今3250-3100年),所揭示的一種獨特青銅文化引起轟動,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隨後,三星堆東城牆、南城牆、月亮灣小城和大型宮殿基址等重要遺蹟也相繼被發現,逐步廓清了三星堆古城分布範圍。專家們認為,三星堆文化面貌既呈現獨特性,又與中原地區、長江中游地區夏商時期古文化有著緊密聯繫
三星堆遺址 入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 大陸傳真 | 兩岸 | 聯合新聞網 https://bit.ly/3kbn92o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