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三教之爭
2014-04-14 15:28:00
泰山佛教經過兩晉對儒、道的依附紮下了根,到了南北朝,儒、釋、道三教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佛教不僅在泰山北麓、 東麓、西麓和徂徠山一帶興起, 繼而自至泰山南麓,寺院經濟也相當發達。由於佛教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畢竟是兩種不同的文化系統; 而釋、 道作為兩種不同的宗教,為爭奪傳播陣地也相互排擠。三教之間,特別是釋儒、釋道之間的鬥爭開始激化。
這一時期的三教之爭,不僅表現為義理之爭,而且還訴諸武力。佛教稱之為「三武之厄」,就有兩次發生在南北朝。太平真君七年(446),北魏太武帝下令焚經毀像,殺盡各地沙門。泰山靈岩寺盡毀, 僧侶大量逃匿。一百多年以後,北周武帝又下詔禁斷釋、道二教,實際上廢佛不廢道,北方寺像掃地悉盡,地論大師法侃,從靈岩寺南逃建康,也有的僧侶從外地潛入泰山之中。
鬥爭並不排斥融合,即所謂「相剋亦相生,相輔亦相成」。道教重今生,追求長生久視,羽化成仙;佛教修來世,追求脫離輪迴的涅槃,這是兩教的重要區別。但肉體成仙難以置信,因此道教不得不吸收佛教有關天堂地獄的思想,道教雖有泰山府君和北斗主管鬼神之說,但還無地獄之說,當下也效法佛教大量引進道經中。源出泰山的渿河,逐漸附會為生死界河,五帝中的青帝,也轉化為執掌生死大權的泰山神,泰山成為陰間王國的首都。
與地獄相對的是天堂,佛教的天堂思想,與道教飛升成仙有吻合之處,道教又加以改造,使佛教所謂的天堂,成為道教神仙所居的仙境,最後定為10大洞天,36小洞天,泰山被列為36小洞天之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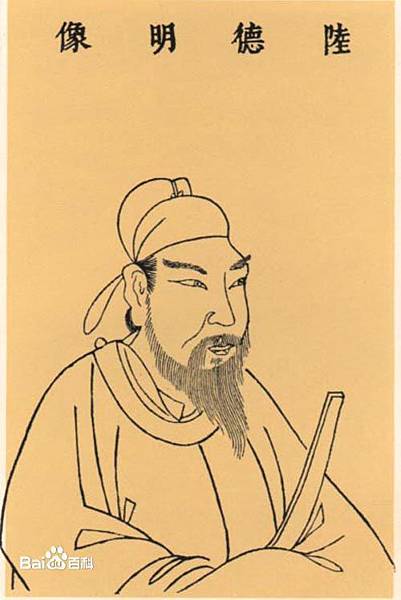
陸德明(550年?-630年),名元朗,表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縣人。中國南朝陳、隋朝、唐朝儒學者。秦王府十八學士之一。
陸德明幼年於受學周弘正。南朝陳太建年間,太子陳叔寶徵集四方名儒於承光殿講義、陸德明年始弱冠,也應邀參加。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恃其貴族身份高談闊論,眾莫敢當;陸德明獨與徐孝克抗對,滿朝賞嘆。後任始興國左常侍、國子助教。陳滅亡後,陸德明歸於鄉里。
隋煬帝嗣位,以陸德明為秘書學士。大業年間,廣為召集明曉經典之士。陸德明與魯達、孔褒都在門下省辯論,無人出陸德明之右者。轉任國子助教。後為皇泰帝楊侗屬下國子司業,入殿侍講經典。王世充稱鄭國皇帝,封其子王玄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還要去陸德明家行束脩之禮。德明深以為恥,先服食了巴豆散,臥於東壁之下。王玄恕入室,跪於床前,陸德明對著遺痢(拉肚子),也不和他說話。之後,去成皋養病,杜絕一切來往應酬。
唐軍平定王世充,陸德明被秦王李世民召為文學館學士,教中山王李承乾經典,任太學博士。轉國子博士,封吳縣男。貞觀三年去世。
著書《經典釋文》30卷、《老子疏》15卷、《易疏》20卷。
其子陸敦信,龍朔年間為左侍極、同東西台三品,封嘉興縣子。
=================================
道家利用為攻擊佛教的依據,也被周世宗引為滅佛理據:"要知道佛教本來就以善化人,如能止於至善,這就是奉佛了。中國大陸佛教信徒佔總人口的9%、中國台灣佛教徒佔總人口的28%、日本佛教徒佔總人口的71%、韓國佛教徒佔總人口的23%、蒙古佛教徒佔總人口的93%,泰國佛教徒佔總人口的94%、柬埔寨佛教徒佔總人口的93%、緬甸佛教徒佔總人口的90%、越南佛教徒佔總人口的50%、斯里蘭卡佛教徒佔總人口的70%。
----------------------------------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中國佛教的發展_我的網站 - https://goo.gl/4IQBX2
陸德明(初唐大臣)_百度百科 - https://goo.gl/ClsJt9
=============
佛、道、儒三教之爭
作者: 不詳
進入東晉以後,佛教大致已在中國初步站穩腳跟,便覺得不能一讓再讓,一忍再忍,於是開始抽出一部分力量來反擊道教的挑戰了。前述元魏僧徒所作《漢法本內傳》,便是這種反擊武器之一。他們造作的不少經典多稱佛——釋迦牟尼為老子並且亦是孔子的老師,甚至更長輩。如東晉名僧支遁在《釋迦文佛像贊序》中說:“昔週姬之末,有大聖號佛;……絡聘週以曾玄。”這樣一來,就不但把佛說成是老子的師父,而且還是他的“太爺”輩;老子和莊子則成了佛的“曾孫”和“玄孫”,連當弟子的資格都不夠了。以後的《正誣論》則說老子聞道於竺乾古先生。古先生即是佛,所以“老子即佛弟子也。”《清淨法行經》又說;“佛遣三弟子(到)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淨光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震旦即中國,儒道的祖師都成了佛弟子的化身,這大概是最早的中國文化西來說。
佛道的祖師問題一直鬧到隋唐宋元之際。武則天時期,佛教比較得勢,有一個僧人就站出來請求銷毀《老子化胡經》。祟佛的武則天還算民主。指定了8名儒生出身的學士討論這個問題;可是得到的結論是:“漢隋諸書所載,不當除削”。直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間(1264—1294年),朝廷還三次組織佛道辯論《化胡經》的真偽。有關記載說,因為元代統治者是“胡人”,便未能容忍詆毀“胡神”。辯論的結果,是道士落髮,《化胡經》連同刻版一起被焚。
東晉至宋元時期佛道徒們的辯論最初還比較有理智,最多也只是吹牛大賽而已;可是。以後竟發展為相互誹謗與謾罵,如佛教徒作《笑道論》,道士則有《道笑論》,言語粗俗,很令人扼腕。佛道之間的矛盾衝突,往往和封建社會的政治矛盾、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形成歷史上多次的滅佛或滅道。如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魏太武帝滅佛,固然有著崔浩、寇謙之慫恿的因素,但太武帝也想通過此舉證明自己親漢不親胡,證明自已是黃帝子孫(拓跋氏自稱是黃帝子昌意的後裔)。有權繼承伏羲、神農的嗣統。又如北周武帝滅佛抑道,也完全是從當時的政治、經濟利益出發,最初未必想焚經毀像,只不過是想排出儒先、道次、釋最後的次序,以證明自己不是五胡,有資格統治漢族罷了。周武帝為此多次召集百官、儒生、道士上殿,讓三教充分發表意見。可是佛教徒卻頗有些“只要主義真”的味道而頻頻進擊,還用阿鼻地獄恐嚇周武帝。周武帝索性答道:只要百姓得樂,我情願去受那地獄諸般苫。話既已說到這一步,閡武帝的滅佛便不可避免了。他一下子毀掉了4萬所以上的寺廟,讓300萬和尚還俗作平民。周齊境內的和尚們這才追悔莫及。
不過,尚須指出的是,南北朝之際,道教雖然排斥佛教,但並不主張殺害佛教徒。從北魏道士寇謙之開始就一直保持著這種態度。公元439年,北魏滅北涼,崇道的魏太武帝捕獲替北涼守城的僧軍3000名,下令剿殺,幸得寇謙之出來說情,3000僧人才倖免於難。446年,魏太武帝又大殺境內僧人。寇謙之向太武帝的寵臣司徒崔浩力勸勿殺,崔浩不聽。但這件事給佛教徒們印像極深。所以後來祟佛的齊文帝宣布滅道教,便僅殺了四名不肯落髮的道士。這以後,周武帝滅佛,亦不肯殺一個僧人。而這應是對佛教自始自終所堅持的和平與平等主義(特別是大乘佛教大慈大悲、普渡眾生的思想)的最好報答。
中國歷史上曠日持久的佛、道、儒三教之爭,始終僅限於“君子動口不動手”,“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範圍內(即使有殺害,也只是懲辦幾位被視為“首惡”者),這大致是中國傳統文化氛圍所使然。因為古代儒家講究中庸、寬容,道家講究清靜無為,而佛教則更是高揚和平與平等的大旗;另外,也是因為佛、道始終未能真正演成國教,未能凌駕於皇權之上而主宰軍國大事。所以,西方有宗教戰爭(基督教的、伊斯蘭教的),一打就是幾十年、上百年、數百年,而中國卻沒有。中國祇有世俗戰爭——皇帝之間的戰爭。軍閥之間的戰爭,皇帝、軍閥同老百姓的戰爭……而沒有宗教之間的戰爭、宗教之間的流血衝突。
從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的傳播活動來看,它既以紮根東土為最高目標,那麼,當它遇到東土的民族宗教的堅決抵抗之時,便沒有將它同後者的鬥爭僅僅看作是兩個宗教之爭,而是將其從根本上處理成兩個先進文明的歷史碰撞。因此,它自始至終都未敢向後者抱以敵意甚而取你死我活的鬥爭態度。其間的某些交鋒甚至激烈的或過火的交鋒,也主要出於向後者表明自己宗教的主旨,表明自己渴求在中華大地上與後者交流、溝通並能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育、開花、結果的願望。加之中華民族固有的開放機制與和諧心理的作用,以及其時中國文化系統正處於一種“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獲”的佳境之際(從漢代一直到明初都是如此),因而佛、道二教之間的關係實際一直是既對立又統一、既鬥爭又調和,且以統一與調和為主要特徵的。
“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兩大最為古老和優秀的文明系統所擁有的看似對立的兩大宗教文化最終在同一塊土地上相揖為友,互相攙持,互相關照,並蒂開放,這在人類宗教文化史上似乎是絕無僅有的現象。而這,又只有在中華土地上才能出現。
-------------------------------
三教之爭與三教融合 (2013-08-24 14:45:20)
三教之爭與三教融合
自董仲舒以來,獨尊儒術,儒教作為正統文化的代表,不僅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且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以“天不變道亦不變”為圭臬,把三綱五常作為不可動搖的天道人倫秩序,尊天命(君權天授、禍福天定)、奉先祖(慎終追遠、祭祀祖宗)、崇聖賢(尊崇儒聖、奉習五經),奠定了儒教哲學的思想基礎。時至魏晉,佛、道興盛,玄風飆起,儒家思想獨尊之說發生了根本的動搖,但在思想文化領域仍然保持其持續的影響和正統地位。儒學也以其固有的兼包並容的特性,在一定的範圍內接納佛、道。但是,不同文化的衝突,無論是在實踐還是在理論上都在所難免。如《牟子理惑論》既表明時代精神之轉換,也反映了外來宗教同本土文化的衝突。當然也在衝突中交相滲透。
佛教得莊、老之滋養,玄學化的佛教哲學在理論上佔有明顯的優勢,其談空說有,理致幽玄,不僅高於古代儒學,較之儒道合流的玄學也略勝一籌。即使在玄學風行之時,般若性空、涅槃佛性之說也代表了當時哲學的最高水平。不過佛教畢竟是外來文化,其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乃至生活習俗,與中國傳統心理無處不存在矛盾、衝突而受主流文化的排拒。所以佛教對儒、道兩家的反擊,一方面顯示自身的存在價值,另一方面也逐漸對自身理論予以適應性的改造,從而推進佛教哲學中國化的過程。
一、儒釋之爭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釋兩教在思想領域內有過多次交鋒,並在爭論中交融互補。
沙門敬不敬王者之爭
西晉佛學,因名士之推崇,與玄風互相煽動,般若理趣,同符老、莊,但帝王仍無奉佛者,沙門亦多胡人。至東晉,明帝、成帝雅好佛法,安帝親接法事。名僧風格,酷肖清流,支遁等僧人立身行事在在與清談契合,而成為清談之領袖。廬山慧遠聞名遐邇。佛寺“乃至一縣數千”(《恆太尉與僚屬沙汰僧眾教書》)。佛教勢力的增強導致與王權、名教的摩擦,首先與朝儀發生抵觸,引發一場沙門敬不敬王者之爭論,圍繞禮儀問題討論夷夏同異,旁及其他。三教衝突發端於此。
在印度,佛教徒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他們禮拜佛祖,而對世俗任何人,包括帝王和父母都不跪拜,甚至還可以接受父母的跪拜。這種教儀與天、祖、聖合一的傳統綱常倫理相悖,也是佛教備受責難,必須改造的課題。東晉成帝時庾冰、何充輔政,前者反佛,後者崇佛。庾冰代帝作詔書,令沙門跪拜王者,認為名教不可棄,禮典不可違,禮敬乃“為治之綱”,又謂“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沙門不敬王者,將破壞禮制的尊嚴與統一,力圖恢復“王教”和獨尊儒術的局面。何充等人則力言佛教乃修善之法,“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不如“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充分發揮佛教輔政治國的作用。何充等還說:“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沙門雖然禮儀有殊,但尊重王權,“每見燒香咒願,必先國家,欲福佑之隆,情無極已”。所以,跪拜與否只是枝節,應許存異。由於何充的反對,庾冰議寢,沙門最終不施禮敬。
東晉安帝時,桓玄總理政事,重提沙門敬王舊事,並以其書示慧遠。慧遠以佛教界權威的身份,明確表示佛教讚譽王化的立場,闡述佛法與世法小異大同的關係。他在答桓玄的書中說:“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再三之訓,彰於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又說“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可見,慧遠認為出家修道者的禮儀同世俗有所不同,但形乖而實同,不失孝敬之義,且有助於政教。中國佛教徒既應嚴守佛教的獨立性,又要依附王權,與傳統禮教保持一致。由於慧遠社會地位的影響,桓玄最終不能強迫沙門禮拜王者。(資料引文見《弘明集》卷十二)
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除了重申在家奉法不違禮,出家修行不失敬的論點以外,還強調,沙門超俗,釋優於儒,周孔之道是方內之教,不關視聽以外,而釋教超言絕象;從追求終極真理的角度來看,佛教是先合後乖,而後隨時制宜,靈活應用,以合世教;堯孔則是先乖後合,因俗施教,有治世之功,長久累積,終歸大道。如此說來,佛儒殊途同歸,但最終歸向卻是佛教。因為佛法兼動靜、合內外、貫理事;堯孔乃有形之教,只能被佛法所包容而不能兼明內外之道。於是,禮制的爭論上升而為儒釋優劣的爭論。這是不能不辨,卻又永無一致結論的問題。
與此相關,還有沙門服飾問題,孝道問題的爭論。其實質還是關於傳統文化與外來佛教文化能否協調共存的問題。儒教以孝為人倫之首,魏晉統治者標榜以孝治天下,天竺佛教追求個人解脫,視家庭為樊籠,剃髮出家,與世絕緣。他們說:“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孝道要求“子之事親,生則致其善,沒則奉其祀。三千之則,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疏,刓剃鬚髮,殘其天貌”,“此大乖於世教”。孫綽的回應是:“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夫緣督以為經,守柔以為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 (孫綽《喻道論》)《禮記》有大孝榮親,博施濟眾的說法,孝道並不限於生養死藏。孫綽據此發揮,說佛教奉養不僅能光宗耀祖,而且自度度人,使天下相安無事,應視為大孝。再者,若有兄弟,則服養、弘道二者兼得。他還指出,“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為事,殷勤之旨可謂至矣”。(引文見《弘明集》卷三)
白黑論之爭
這次沖突發生在劉宋時期。還俗沙門慧琳作《白黑論》(又稱《均善論》),設白學先生、黑學道士之問答,論孔釋異同,貶黜佛學。無神論者何承天大加讚賞,並送宗炳,宗復書斥慧琳之妄。此即白黑之爭。
首先論及“空”義。黑說:“釋氏即物為空,空物為一”。白問:“釋氏空物,物信空邪?”黑答,不只是空,而且是空又空。白問:三儀萬品就在宇宙天地間,怎能是空?黑答:“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事物“興滅無常,因緣無主”,“事用”雖有,“性理”則空。於是白學先生說:“今析豪空樹,無傷垂蔭之茂,離材虛室,不損輪奐之美。”(《宋書•蠻夷傳》)慧琳以白學先生之口吻,指出佛教般若學雖創造一大堆範疇論證萬物自性空而無實,但是絲毫無損事物的實際性質與勃勃生機。
宗炳反駁慧琳說:“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眾緣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 ”又說:“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宗炳以事物的可析性與變動性否定事物自身的實在性,顯然與僧肇《不真空論》相合。關於佛教以有欲邀無欲的問題,宗炳辯解說:“泥恆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可謂“獲利於無利”,“有欲於無欲”。何承天未能對性空學說提出有力的批判,但駁斥了宗炳的無欲無利說,指出:既然“泥洹以離苦為樂,法身以接善為身”, 那麼,“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在這個問題上,何承天顯然佔據上風,因為世界上只有超功利主義,卻沒有超功利的事實,問題只在於功利的正當與否,佛教追求安樂解脫的本身也是一種利欲。這正是何承天批評佛教的事實根據。
白黑之爭還有涉及形神等問題,見以下相關部分。
報應論之爭
報應問題實質就是命運問題,從東晉起,便成為思想界論爭的焦點。人之吉凶禍福、富貴貧賤、生死壽夭因何而生?雖說是福善禍淫,卻為何善惡與禍福並不相應?傳統的解釋基本上有兩種:一是天命論,即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人只能樂天知命,安於所受。此說取消了個人的能動性和糾正或改造社會不公正的責任,缺乏理論上的說服力。二是福善禍淫說,即冥冥中有賞善罰惡的主體,並且賞罰延及子孫後世。《周易》有“積善餘慶,積惡餘殃”之說,流傳甚廣。但現實生活中善惡不得其報,甚至報不當報的事實比比皆是,子孫受報的說法同樣缺乏事實根據。於是佛教乘虛而入,給予福善因果全新的解釋,即因果報應、三世輪迴。初起之時,人們常以傳統觀念予以界說,乃至曲解。如孫綽《喻道論》說:“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例如“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所致邪?”這是儒家的報應論,而非佛教的果報論。
對佛教報應論做出自圓其說解釋的是慧遠。當時戴逵作《釋疑論》,反對報應說,主張命定論。他給慧遠弟子周續之的信中指出,報應之說無驗於事實,禍福之報常與現實不合。周續之作書答戴逵說,“福善莫驗”的現像也曾使他迷惑,求儒不能解,故轉求佛學,才“昭然有歸”(《廣弘明集》卷十八)。但周續之對佛教報應之說未能作系統論述,於是慧遠將舊作《三報論》投寄戴逵,實際上是對報應問題的全面闡述。文曰:“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 肯定善惡遲早有報,絲毫不爽。如此也就把報應與現實不符的矛盾,消解在無限延長的時間長河之中,也給予“心”作為報應的主體地位。
慧遠的三世報應論有兩大特點:一是雖說報應必有,但不受時間限制,把必然性寓於無限延長的偶然性之中,偶然也就變成了必然。二是強調報應無主,乃由心感於事而生,彷彿是一種自然的因果關係,遂使佛教報應說具有客觀規律的外觀。慧遠還提到:“世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令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眾塗而駭其異。”三報論既符合佛教緣生之理,說明已做不失,未做不得,遇緣成果,自作自受,又對報不當報的社會現實作出了看似合理的解釋,比儒教福善禍淫之說更圓通、高明,比宿命論要積極、靈活,也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時至劉宋,《白黑論》對佛教的因果報應說也進行了批判。文借白學先生之口說:“美泥洹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群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開利竟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既然佛教以空無立義,因果卻用福樂設教,如此增加了人們的利欲之心,豈非自相矛盾?揭示佛教禁慾主義說教與施善求報、苦修成佛之間的矛盾。黑學道士辯之曰:“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來生報應只是權宜方便之說。白學先生進而指出:“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人們大興土木,獻財事佛,都是為了求得將來的福利,哪裡會心性空寂呢?其實這正是宗教組織目的與手段的二律悖反。
繼白黑爭論之後,何承天又作《達性論》,與顏延之往復問難(事載《弘明集》卷四)。《達性論》以儒家的三才說,對抗佛教的眾生說。何承天強調人為萬物之靈,在天地萬物造化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不可與其它眾生等同。儒家祭祀用牲,王狩取獸,役物以養生,漁獵而有食,都不能絕對禁殺,只需強調順時少取,而不可行佛教的絕對禁殺。顏延之答書雖然承認人與生物有異,但說眾品同於有生,重申報應是客觀必然的規律,“物無妄然,各以類感”,善惡之報“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承天對此提出質疑,內容無非是因果乖錯,所報遲速相去深遠,甚至百生千生之遙。
其實,《達性論》的爭論,實際上表現了人道主義與神道主義之間的對立。何承天重視人和人生,引導人們關注現實,鼓勵人們相信自身的創造力,摒棄關於來世幸福的幻想,顯然是入世的。顏延之利用儒家神學資料附會佛學,“引釋符姬”駁斥何承天的“立姬廢釋”,也說明佛儒在在終極關懷上的一致性。另外還有劉少府針對何承天《報應問》辯論因果(載《廣弘明集》卷十八),凡此種種,內容大同小異,不再轉述。
因果報應之辯,雖然在理論上,佛教衛道之士未能徹底征服儒家弟子,但是因果報應並非耳目取證和理性思考的結果,而是心理上的需要。佛教不僅沒有在這場爭論中相形見絀,反而在積極參與中擴大了自身的影響。
神滅神不滅論之爭
慧遠結合中國傳統的靈魂說與佛教輪迴說,作《形盡神不滅》文,提出神不滅論和形神二元論。他說:“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神妙形粗不應同滅,這是其後神不滅論者常用的理論依據。他又指出:“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將本來屬於無神論的薪火之說,引申為神不滅論的喻證。
對此,何承天說:“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這裡何氏沿襲早期神滅論形神觀之舊說,宗炳以形神二元論予以反擊。他不採用慧遠改造的薪火之喻以說形神,因為火賴於薪,神則不生於形,所以他從五個方面論證了神妙形粗,神不隨形毀而滅的論點(見《明佛論》)。
其一,群生之神,本已有之。他說:“生育之前素有粗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
其二,形神並非同步不離,如果形生則神生,形滅則神滅,那麼必然是形殘神毀,形病神困,但是實際情況則是有很多人形傷殘而神意平全,病之極而無變德行之主。
其三,精神微妙無比,非粗糙的形體所能比擬。聖賢的形體與愚人並無甚差異,而其特異之處正在於其精神超越,故神不應與形體同生滅。
其四,儒家承認神靈不滅,如“周公郊祀后稷,宗稷文王”,“則文、稷之靈,不可謂滅也” 。
其五,不憶前生,無害精神本有。這是從反面證明神不滅的合理性。他舉例說,剛長牙的孩子都不記得在母親胎中之事,可見一生之事都難以記憶,何況經歷生死?不記得前生也不能說就是“神滅”。
神滅與神不滅爭論的高潮,發生在齊梁時期。爭論雙方是范縝與肖子良。二人以討論造成貧富貴賤產生原因的現實問題始,進而討論因果報應之有無,最終以神滅神不滅為爭論的焦點。范縝以偶然論批判因果報應學說,但是為了從根本上破斥因果報應說的根據,故“退而著《神滅論》”。此論一出,朝野嘩然,“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梁書•范縝傳》)。范縝的神滅論繼承了先秦以來的形滅神亡的思想傳統,把魏晉玄學的“本末”“體用”概念應用於形神觀。他提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用,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這種形質神用的觀點,進一步明確了形體與精神是本體與作用的關係,肯定了精神對本體的依賴性。鑑於“薪火之喻”為佛教擁護者所用,故范縝捨棄薪火之喻,改用“刃利之喻”,將形與神比作刀刃和鋒利,進一步明確精神是人體功能的論點,論證形神相與不二,靈魂不能離開肉體獨立存在的觀點。
神滅神不滅的爭論,看似有神論與無神論,或者說唯心與唯物的衝突,其實佛教緣生之理無疑是對“有神論”的否定。對佛教的責難,關鍵在於對“神”的理解不同,二者優劣高下實在難分軒輊。無論怎樣講,這場爭論最終的結果,和其它爭論一樣,事實上在衝突中推動了儒佛的交融滲透,也促進了它們在哲學思維方面的深入發展,反映了不同文化趨同的總體態勢。佛教哲學也在對儒家挑戰的回應中,逐步實現它的中國化的過程。
二、佛道關係
佛教和道教在南北朝時期開始廣泛流傳,在思想文化界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們之間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並在競爭中發展。
夷夏論之爭
南朝宋末道士顧歡作《夷夏論》。他說:“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其入不同,其為必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是車可涉川而舟可行陸乎?”關於佛道優劣,他說:“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粗人可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言辭雖委婉,揚道抑佛的態度不言自明。雖然缺乏理論上的價值,但它代表了一部分人維護傳統文化尊嚴、鄙夷和排斥外來文化的一種民族情緒,所以在社會上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的,並由此把夷夏之辨,推向高潮。論辨雙方雖然也涉及到一些理論問題,但重點在民族、地域、民俗、禮俗方面,門戶之見尤在所難免,無須贅述。
《三破論》與《辨惑論》之爭
南齊有道士假張融作《三破論》,激烈攻擊以至漫罵佛教(《弘明集》卷八《滅惑論》引)。劉勰、僧順、玄光等著論駁斥。這場辯論是夷夏之爭的繼續。《三破論》說:佛教“入國破國”,使“國空民窮”;“入家破家”、“入身破身”,“遺棄二親”,違背孝道;佛教乃羌胡之教, “剛強無禮,無異禽獸”;佛教是“學死”之術,而道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
劉勰 著《滅惑論》逐一駁斥。指出:國之衰破不在佛法,塔寺之興,闡揚聖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孝之理“由乎心,無係於發”,佛教徒“棄跡求心”,是棄小孝而盡大孝。佛道相比,“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神識無窮”。同時指出,道分三品:“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老子“著書論道,貴在無為,理歸靜一,化本虛柔”,“斯乃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神仙小道,未能免有漏無終;至於張陵張魯之徒,“醮事章符,設教五斗”,邪偽已甚,“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乃“傷政萌亂”之道。《滅惑論》雖有門戶之見,但論夷夏相通及道家三品之說,還是很有見地的。《笑道論》與《二教論》之爭
周武滅佛,也出現了生動的理論爭辯。天和五年(570年),甄鸞上《笑道論》,道安又上《二教論》激烈批判道教,朝宰無辯之者,迫使武帝不得不暫時擱置排佛之舉。
《笑道論》的特色在於揭露道書的荒謬,說道書記述互相矛盾、內容違背歷史常識、更有男女合氣之法,穢不可聞(《道士合氣三十五》),以及多剽竊佛經諸子書等等。攻擊之語甚烈,但所述內容也可說是據實徵引。
道安的《二教論》由於吸收了江南佛教學者的辯論成果,理論色彩比較濃。要點如下:第一,反對“三教”提法,只承認有內外二教。“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典,典號為內”,“釋教為內,儒教為外”。“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硌硌,總括九流”,道教只能算儒的支流。第二,佛教高於孔老。佛教“近超生死,遠澄泥洹”,乃“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推色盡於極微,老氏未辨;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第三,儒優於道,孔聖而老賢。“老氏之旨本救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而不可治國。第四,道優仙劣。老子“虛無為本,柔弱為用”,自有其價值,“若乃煉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屍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第五,佛優仙劣。他反對“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的佛道調和論,認為佛道根本不同:“佛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餌以養生”。涅槃超出生死,非道教長生所能比擬。第六,老學優而鬼道劣。他引用南齊釋玄光的《辨惑論》說:“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鬼籙之談”、“巫覡之說”,“訛惑生民,敗傷王教”。第七,道書剽竊佛經。“《黃庭》、《元陽》,採撮《法華》,以道換佛,改用尤拙。第八,批判社會上流行的各種反佛觀點,斥“人死神滅,更無來生”為“斷見”,斥“聚散莫窮,心神無間”為“常見”,斥“吉凶苦樂皆天所為”為“他因外道”,斥“諸法自然,不由因得”為“無因外道”等,重在辨異,反對合同。但他對孔老的肯定,對丹鼎符籙、屍解形化的仙道、鬼道違背了老莊立言之本的論說,無疑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反映了佛道在哲學理論上的追求。
三教爭論固然此起彼伏,然而完全排斥的偏激主張並不占主流。爭論中三教相互碰撞,也相互吸收,並在碰撞和吸收中改變著對方也改變著自己,促進了三教融合與趨同。
三、三教融合論
一為本末內外論,二為均善均聖論,三為殊途同歸論。
本末內外論。
本末內外的範疇由玄學家作了充分闡述。王弼以本末統一儒道,郭像以內外統一孔莊。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對三教融合產生了重大影響。慧遠以“內外”調和佛儒,說“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沙門不敬王者論》)。宋文帝以儒治國,以佛煉神的說法類似郭象的“內聖外王之道”,不過內聖不是老莊而是佛學罷了。北周道安將佛儒視為內外二教,佛教為內,孔老為外。外亦稱世教,有時單指儒教。內外關係也是本末關係,三教自然要以佛教為本。
道教和道教人士論道儒或道佛關係時,多講本末。東晉道士葛洪在《抱朴子•明本》中說:“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道教學者有時也接受內外分類法,以道教為內學,故道教著作為“內篇”;以道教以外的學說為外學。
從儒學陣營看,自然強調儒為本,其他為末。所謂“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晉書•傅玄傳》)。宋何承天以為“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而佛教不過是一個支流。北周武帝滅佛前亦想調和三教關係,曾宣布“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周書•武帝上》)。總之,三教都講本末內外論,但對“本”的理解不同,目的在於鞏固自身的核心地位,並在此基礎上統合三教。後世雖然儒教哲學始終佔據統治地位,但三教一體、諸宗合流的總體趨勢,也是這一時期融合論發展的必然結果。
均善論或均聖論
與本末內外論相比較,此論更強調三教和同,調融三家的傾向更為明顯。它承認三教各有其用,也各有其不足或流弊。東晉戴逵評論儒道時說,儒家“本以興賢也,即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道家“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晉書•隱逸•戴逵傳》)。宋沙門慧琳的《白黑論》雖然批評了佛教性空觀與報應說,但不否定佛教的勸善功用,主張“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宋書•蠻夷傳》)。梁武帝在《述三教師》中也說,“窮源無二聖,測則非三英”,“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認為三教雖有深淺之別,而向善實無不同。
殊途同歸論
殊途同歸論也包括了本末內外論和均善均聖論,但本末內外論存同而重異,以本為主,以內為主,本末內外是不平等的;均善均聖論則是存異而重同,以三教為平等;殊途同歸論則是先異而後同,或者跡異而理同,承認三教在形式、禮儀、方法上的差別,甚至對立,但認為在基本原理和終極關懷上卻是一致的。故謂之“殊途同歸論”。其說有三:第一,殊途同歸,歸在至理。第二,殊途同歸,歸在有神。第三,殊途同歸,歸在教化。第三點最為盛行。韋敻在奏獻周武帝的《三教序》中說,“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周書•韋敻傳》),都講勸善化俗,而且善惡標準一致,都是以儒家的綱常名教準則,所以三教同歸,實際上是歸於儒家的教化。這裡雖然突出的是儒教的主導地位,但是殊途同歸之說便於克服對外來文化,具體說就是佛教的拒斥心理,冷靜思考、比較三教異同,異中求同,求同存異,顯然有利於佛教的傳播和三教的匯通與融合。
三教融合論盛行,道教與儒教聯盟,依傍儒教而壯大;同時又用道家思想溝通佛、道的理論,在拒斥中吸收佛教義理,而使道教在哲學上有所昇華。其後“重玄”的道教之哲學建構,無疑得力於玄學化的佛教哲學。
佛教作為外來文化,在漢末,依附黃老方術而得以植根和流布,魏晉時期又藉助玄學豐富自己的理論而得以發展。佛教玄學化,實際上就是三教在哲理上的融合,也是中國化佛教形成的前驅先路。在這個過程中,佛教自覺地實行自身的改造,在政治上忠君,在倫理上主“孝”,在理論上主張和而不同,實行儒外佛內的分工合作,把事功留給儒教,把內聖的任務轉歸佛法,佛儒調協,使天下歸心。這也是中國宗教哲學發展的總體態勢。
三教之爭與三教融合
(2013-08-24 14:45:20)三教之爭與三教融合
自董仲舒以來,獨尊儒術,儒教作為正統文化的代表,不僅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且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以“天不變道亦不變”為圭臬,把三綱五常作為不可動搖的天道人倫秩序,尊天命(君權天授、禍福天定)、奉先祖(慎終追遠、祭祀祖宗)、崇聖賢(尊崇儒聖、奉習五經),奠定了儒教哲學的思想基礎。時至魏晉,佛、道興盛,玄風飆起,儒家思想獨尊之說發生了根本的動搖,但在思想文化領域仍然保持其持續的影響和正統地位。儒學也以其固有的兼包並容的特性,在一定的範圍內接納佛、道。但是,不同文化的衝突,無論是在實踐還是在理論上都在所難免。如《牟子理惑論》既表明時代精神之轉換,也反映了外來宗教同本土文化的衝突。當然也在衝突中交相滲透。
佛教得莊、老之滋養,玄學化的佛教哲學在理論上佔有明顯的優勢,其談空說有,理致幽玄,不僅高於古代儒學,較之儒道合流的玄學也略勝一籌。即使在玄學風行之時,般若性空、涅槃佛性之說也代表了當時哲學的最高水平。不過佛教畢竟是外來文化,其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乃至生活習俗,與中國傳統心理無處不存在矛盾、衝突而受主流文化的排拒。所以佛教對儒、道兩家的反擊,一方面顯示自身的存在價值,另一方面也逐漸對自身理論予以適應性的改造,從而推進佛教哲學中國化的過程。
一、儒釋之爭
魏晉南北朝時期儒釋兩教在思想領域內有過多次交鋒,並在爭論中交融互補。
沙門敬不敬王者之爭
西晉佛學,因名士之推崇,與玄風互相煽動,般若理趣,同符老、莊,但帝王仍無奉佛者,沙門亦多胡人。至東晉,明帝、成帝雅好佛法,安帝親接法事。名僧風格,酷肖清流,支遁等僧人立身行事在在與清談契合,而成為清談之領袖。廬山慧遠聞名遐邇。佛寺“乃至一縣數千”(《恆太尉與僚屬沙汰僧眾教書》)。佛教勢力的增強導致與王權、名教的摩擦,首先與朝儀發生抵觸,引發一場沙門敬不敬王者之爭論,圍繞禮儀問題討論夷夏同異,旁及其他。三教衝突發端於此。
在印度,佛教徒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他們禮拜佛祖,而對世俗任何人,包括帝王和父母都不跪拜,甚至還可以接受父母的跪拜。這種教儀與天、祖、聖合一的傳統綱常倫理相悖,也是佛教備受責難,必須改造的課題。東晉成帝時庾冰、何充輔政,前者反佛,後者崇佛。庾冰代帝作詔書,令沙門跪拜王者,認為名教不可棄,禮典不可違,禮敬乃“為治之綱”,又謂“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沙門不敬王者,將破壞禮制的尊嚴與統一,力圖恢復“王教”和獨尊儒術的局面。何充等人則力言佛教乃修善之法,“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不如“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充分發揮佛教輔政治國的作用。何充等還說:“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沙門雖然禮儀有殊,但尊重王權,“每見燒香咒願,必先國家,欲福佑之隆,情無極已”。所以,跪拜與否只是枝節,應許存異。由於何充的反對,庾冰議寢,沙門最終不施禮敬。
東晉安帝時,桓玄總理政事,重提沙門敬王舊事,並以其書示慧遠。慧遠以佛教界權威的身份,明確表示佛教讚譽王化的立場,闡述佛法與世法小異大同的關係。他在答桓玄的書中說:“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再三之訓,彰於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又說“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可見,慧遠認為出家修道者的禮儀同世俗有所不同,但形乖而實同,不失孝敬之義,且有助於政教。中國佛教徒既應嚴守佛教的獨立性,又要依附王權,與傳統禮教保持一致。由於慧遠社會地位的影響,桓玄最終不能強迫沙門禮拜王者。(資料引文見《弘明集》卷十二)
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除了重申在家奉法不違禮,出家修行不失敬的論點以外,還強調,沙門超俗,釋優於儒,周孔之道是方內之教,不關視聽以外,而釋教超言絕象;從追求終極真理的角度來看,佛教是先合後乖,而後隨時制宜,靈活應用,以合世教;堯孔則是先乖後合,因俗施教,有治世之功,長久累積,終歸大道。如此說來,佛儒殊途同歸,但最終歸向卻是佛教。因為佛法兼動靜、合內外、貫理事;堯孔乃有形之教,只能被佛法所包容而不能兼明內外之道。於是,禮制的爭論上升而為儒釋優劣的爭論。這是不能不辨,卻又永無一致結論的問題。
與此相關,還有沙門服飾問題,孝道問題的爭論。其實質還是關於傳統文化與外來佛教文化能否協調共存的問題。儒教以孝為人倫之首,魏晉統治者標榜以孝治天下,天竺佛教追求個人解脫,視家庭為樊籠,剃髮出家,與世絕緣。他們說:“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孝道要求“子之事親,生則致其善,沒則奉其祀。三千之則,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疏,刓剃鬚髮,殘其天貌”,“此大乖於世教”。孫綽的回應是:“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夫緣督以為經,守柔以為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 (孫綽《喻道論》)《禮記》有大孝榮親,博施濟眾的說法,孝道並不限於生養死藏。孫綽據此發揮,說佛教奉養不僅能光宗耀祖,而且自度度人,使天下相安無事,應視為大孝。再者,若有兄弟,則服養、弘道二者兼得。他還指出,“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為事,殷勤之旨可謂至矣”。(引文見《弘明集》卷三)
白黑論之爭
這次沖突發生在劉宋時期。還俗沙門慧琳作《白黑論》(又稱《均善論》),設白學先生、黑學道士之問答,論孔釋異同,貶黜佛學。無神論者何承天大加讚賞,並送宗炳,宗復書斥慧琳之妄。此即白黑之爭。
首先論及“空”義。黑說:“釋氏即物為空,空物為一”。白問:“釋氏空物,物信空邪?”黑答,不只是空,而且是空又空。白問:三儀萬品就在宇宙天地間,怎能是空?黑答:“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事物“興滅無常,因緣無主”,“事用”雖有,“性理”則空。於是白學先生說:“今析豪空樹,無傷垂蔭之茂,離材虛室,不損輪奐之美。”(《宋書•蠻夷傳》)慧琳以白學先生之口吻,指出佛教般若學雖創造一大堆範疇論證萬物自性空而無實,但是絲毫無損事物的實際性質與勃勃生機。
宗炳反駁慧琳說:“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眾緣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 ”又說:“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宗炳以事物的可析性與變動性否定事物自身的實在性,顯然與僧肇《不真空論》相合。關於佛教以有欲邀無欲的問題,宗炳辯解說:“泥恆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可謂“獲利於無利”,“有欲於無欲”。何承天未能對性空學說提出有力的批判,但駁斥了宗炳的無欲無利說,指出:既然“泥洹以離苦為樂,法身以接善為身”, 那麼,“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在這個問題上,何承天顯然佔據上風,因為世界上只有超功利主義,卻沒有超功利的事實,問題只在於功利的正當與否,佛教追求安樂解脫的本身也是一種利欲。這正是何承天批評佛教的事實根據。
白黑之爭還有涉及形神等問題,見以下相關部分。
報應論之爭
報應問題實質就是命運問題,從東晉起,便成為思想界論爭的焦點。人之吉凶禍福、富貴貧賤、生死壽夭因何而生?雖說是福善禍淫,卻為何善惡與禍福並不相應?傳統的解釋基本上有兩種:一是天命論,即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人只能樂天知命,安於所受。此說取消了個人的能動性和糾正或改造社會不公正的責任,缺乏理論上的說服力。二是福善禍淫說,即冥冥中有賞善罰惡的主體,並且賞罰延及子孫後世。《周易》有“積善餘慶,積惡餘殃”之說,流傳甚廣。但現實生活中善惡不得其報,甚至報不當報的事實比比皆是,子孫受報的說法同樣缺乏事實根據。於是佛教乘虛而入,給予福善因果全新的解釋,即因果報應、三世輪迴。初起之時,人們常以傳統觀念予以界說,乃至曲解。如孫綽《喻道論》說:“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例如“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所致邪?”這是儒家的報應論,而非佛教的果報論。
對佛教報應論做出自圓其說解釋的是慧遠。當時戴逵作《釋疑論》,反對報應說,主張命定論。他給慧遠弟子周續之的信中指出,報應之說無驗於事實,禍福之報常與現實不合。周續之作書答戴逵說,“福善莫驗”的現像也曾使他迷惑,求儒不能解,故轉求佛學,才“昭然有歸”(《廣弘明集》卷十八)。但周續之對佛教報應之說未能作系統論述,於是慧遠將舊作《三報論》投寄戴逵,實際上是對報應問題的全面闡述。文曰:“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 肯定善惡遲早有報,絲毫不爽。如此也就把報應與現實不符的矛盾,消解在無限延長的時間長河之中,也給予“心”作為報應的主體地位。
慧遠的三世報應論有兩大特點:一是雖說報應必有,但不受時間限制,把必然性寓於無限延長的偶然性之中,偶然也就變成了必然。二是強調報應無主,乃由心感於事而生,彷彿是一種自然的因果關係,遂使佛教報應說具有客觀規律的外觀。慧遠還提到:“世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令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眾塗而駭其異。”三報論既符合佛教緣生之理,說明已做不失,未做不得,遇緣成果,自作自受,又對報不當報的社會現實作出了看似合理的解釋,比儒教福善禍淫之說更圓通、高明,比宿命論要積極、靈活,也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時至劉宋,《白黑論》對佛教的因果報應說也進行了批判。文借白學先生之口說:“美泥洹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群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開利竟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既然佛教以空無立義,因果卻用福樂設教,如此增加了人們的利欲之心,豈非自相矛盾?揭示佛教禁慾主義說教與施善求報、苦修成佛之間的矛盾。黑學道士辯之曰:“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來生報應只是權宜方便之說。白學先生進而指出:“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人們大興土木,獻財事佛,都是為了求得將來的福利,哪裡會心性空寂呢?其實這正是宗教組織目的與手段的二律悖反。
繼白黑爭論之後,何承天又作《達性論》,與顏延之往復問難(事載《弘明集》卷四)。《達性論》以儒家的三才說,對抗佛教的眾生說。何承天強調人為萬物之靈,在天地萬物造化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不可與其它眾生等同。儒家祭祀用牲,王狩取獸,役物以養生,漁獵而有食,都不能絕對禁殺,只需強調順時少取,而不可行佛教的絕對禁殺。顏延之答書雖然承認人與生物有異,但說眾品同於有生,重申報應是客觀必然的規律,“物無妄然,各以類感”,善惡之報“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承天對此提出質疑,內容無非是因果乖錯,所報遲速相去深遠,甚至百生千生之遙。
其實,《達性論》的爭論,實際上表現了人道主義與神道主義之間的對立。何承天重視人和人生,引導人們關注現實,鼓勵人們相信自身的創造力,摒棄關於來世幸福的幻想,顯然是入世的。顏延之利用儒家神學資料附會佛學,“引釋符姬”駁斥何承天的“立姬廢釋”,也說明佛儒在在終極關懷上的一致性。另外還有劉少府針對何承天《報應問》辯論因果(載《廣弘明集》卷十八),凡此種種,內容大同小異,不再轉述。
因果報應之辯,雖然在理論上,佛教衛道之士未能徹底征服儒家弟子,但是因果報應並非耳目取證和理性思考的結果,而是心理上的需要。佛教不僅沒有在這場爭論中相形見絀,反而在積極參與中擴大了自身的影響。
神滅神不滅論之爭
慧遠結合中國傳統的靈魂說與佛教輪迴說,作《形盡神不滅》文,提出神不滅論和形神二元論。他說:“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神妙形粗不應同滅,這是其後神不滅論者常用的理論依據。他又指出:“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將本來屬於無神論的薪火之說,引申為神不滅論的喻證。
對此,何承天說:“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這裡何氏沿襲早期神滅論形神觀之舊說,宗炳以形神二元論予以反擊。他不採用慧遠改造的薪火之喻以說形神,因為火賴於薪,神則不生於形,所以他從五個方面論證了神妙形粗,神不隨形毀而滅的論點(見《明佛論》)。
其一,群生之神,本已有之。他說:“生育之前素有粗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
其二,形神並非同步不離,如果形生則神生,形滅則神滅,那麼必然是形殘神毀,形病神困,但是實際情況則是有很多人形傷殘而神意平全,病之極而無變德行之主。
其三,精神微妙無比,非粗糙的形體所能比擬。聖賢的形體與愚人並無甚差異,而其特異之處正在於其精神超越,故神不應與形體同生滅。
其四,儒家承認神靈不滅,如“周公郊祀后稷,宗稷文王”,“則文、稷之靈,不可謂滅也” 。
其五,不憶前生,無害精神本有。這是從反面證明神不滅的合理性。他舉例說,剛長牙的孩子都不記得在母親胎中之事,可見一生之事都難以記憶,何況經歷生死?不記得前生也不能說就是“神滅”。
神滅與神不滅爭論的高潮,發生在齊梁時期。爭論雙方是范縝與肖子良。二人以討論造成貧富貴賤產生原因的現實問題始,進而討論因果報應之有無,最終以神滅神不滅為爭論的焦點。范縝以偶然論批判因果報應學說,但是為了從根本上破斥因果報應說的根據,故“退而著《神滅論》”。此論一出,朝野嘩然,“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梁書•范縝傳》)。范縝的神滅論繼承了先秦以來的形滅神亡的思想傳統,把魏晉玄學的“本末”“體用”概念應用於形神觀。他提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用,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這種形質神用的觀點,進一步明確了形體與精神是本體與作用的關係,肯定了精神對本體的依賴性。鑑於“薪火之喻”為佛教擁護者所用,故范縝捨棄薪火之喻,改用“刃利之喻”,將形與神比作刀刃和鋒利,進一步明確精神是人體功能的論點,論證形神相與不二,靈魂不能離開肉體獨立存在的觀點。
神滅神不滅的爭論,看似有神論與無神論,或者說唯心與唯物的衝突,其實佛教緣生之理無疑是對“有神論”的否定。對佛教的責難,關鍵在於對“神”的理解不同,二者優劣高下實在難分軒輊。無論怎樣講,這場爭論最終的結果,和其它爭論一樣,事實上在衝突中推動了儒佛的交融滲透,也促進了它們在哲學思維方面的深入發展,反映了不同文化趨同的總體態勢。佛教哲學也在對儒家挑戰的回應中,逐步實現它的中國化的過程。
二、佛道關係
佛教和道教在南北朝時期開始廣泛流傳,在思想文化界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們之間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並在競爭中發展。
夷夏論之爭
南朝宋末道士顧歡作《夷夏論》。他說:“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其入不同,其為必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是車可涉川而舟可行陸乎?”關於佛道優劣,他說:“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粗人可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言辭雖委婉,揚道抑佛的態度不言自明。雖然缺乏理論上的價值,但它代表了一部分人維護傳統文化尊嚴、鄙夷和排斥外來文化的一種民族情緒,所以在社會上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的,並由此把夷夏之辨,推向高潮。論辨雙方雖然也涉及到一些理論問題,但重點在民族、地域、民俗、禮俗方面,門戶之見尤在所難免,無須贅述。
《三破論》與《辨惑論》之爭
南齊有道士假張融作《三破論》,激烈攻擊以至漫罵佛教(《弘明集》卷八《滅惑論》引)。劉勰、僧順、玄光等著論駁斥。這場辯論是夷夏之爭的繼續。《三破論》說:佛教“入國破國”,使“國空民窮”;“入家破家”、“入身破身”,“遺棄二親”,違背孝道;佛教乃羌胡之教, “剛強無禮,無異禽獸”;佛教是“學死”之術,而道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
劉勰 著《滅惑論》逐一駁斥。指出:國之衰破不在佛法,塔寺之興,闡揚聖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孝之理“由乎心,無係於發”,佛教徒“棄跡求心”,是棄小孝而盡大孝。佛道相比,“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神識無窮”。同時指出,道分三品:“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老子“著書論道,貴在無為,理歸靜一,化本虛柔”,“斯乃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神仙小道,未能免有漏無終;至於張陵張魯之徒,“醮事章符,設教五斗”,邪偽已甚,“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乃“傷政萌亂”之道。《滅惑論》雖有門戶之見,但論夷夏相通及道家三品之說,還是很有見地的。《笑道論》與《二教論》之爭
周武滅佛,也出現了生動的理論爭辯。天和五年(570年),甄鸞上《笑道論》,道安又上《二教論》激烈批判道教,朝宰無辯之者,迫使武帝不得不暫時擱置排佛之舉。
《笑道論》的特色在於揭露道書的荒謬,說道書記述互相矛盾、內容違背歷史常識、更有男女合氣之法,穢不可聞(《道士合氣三十五》),以及多剽竊佛經諸子書等等。攻擊之語甚烈,但所述內容也可說是據實徵引。
道安的《二教論》由於吸收了江南佛教學者的辯論成果,理論色彩比較濃。要點如下:第一,反對“三教”提法,只承認有內外二教。“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典,典號為內”,“釋教為內,儒教為外”。“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硌硌,總括九流”,道教只能算儒的支流。第二,佛教高於孔老。佛教“近超生死,遠澄泥洹”,乃“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推色盡於極微,老氏未辨;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第三,儒優於道,孔聖而老賢。“老氏之旨本救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而不可治國。第四,道優仙劣。老子“虛無為本,柔弱為用”,自有其價值,“若乃煉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屍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第五,佛優仙劣。他反對“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其揆一也”的佛道調和論,認為佛道根本不同:“佛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餌以養生”。涅槃超出生死,非道教長生所能比擬。第六,老學優而鬼道劣。他引用南齊釋玄光的《辨惑論》說:“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鬼籙之談”、“巫覡之說”,“訛惑生民,敗傷王教”。第七,道書剽竊佛經。“《黃庭》、《元陽》,採撮《法華》,以道換佛,改用尤拙。第八,批判社會上流行的各種反佛觀點,斥“人死神滅,更無來生”為“斷見”,斥“聚散莫窮,心神無間”為“常見”,斥“吉凶苦樂皆天所為”為“他因外道”,斥“諸法自然,不由因得”為“無因外道”等,重在辨異,反對合同。但他對孔老的肯定,對丹鼎符籙、屍解形化的仙道、鬼道違背了老莊立言之本的論說,無疑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反映了佛道在哲學理論上的追求。
三教爭論固然此起彼伏,然而完全排斥的偏激主張並不占主流。爭論中三教相互碰撞,也相互吸收,並在碰撞和吸收中改變著對方也改變著自己,促進了三教融合與趨同。
三、三教融合論
一為本末內外論,二為均善均聖論,三為殊途同歸論。
本末內外論。
本末內外的範疇由玄學家作了充分闡述。王弼以本末統一儒道,郭像以內外統一孔莊。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對三教融合產生了重大影響。慧遠以“內外”調和佛儒,說“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沙門不敬王者論》)。宋文帝以儒治國,以佛煉神的說法類似郭象的“內聖外王之道”,不過內聖不是老莊而是佛學罷了。北周道安將佛儒視為內外二教,佛教為內,孔老為外。外亦稱世教,有時單指儒教。內外關係也是本末關係,三教自然要以佛教為本。
道教和道教人士論道儒或道佛關係時,多講本末。東晉道士葛洪在《抱朴子•明本》中說:“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道教學者有時也接受內外分類法,以道教為內學,故道教著作為“內篇”;以道教以外的學說為外學。
從儒學陣營看,自然強調儒為本,其他為末。所謂“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晉書•傅玄傳》)。宋何承天以為“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而佛教不過是一個支流。北周武帝滅佛前亦想調和三教關係,曾宣布“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周書•武帝上》)。總之,三教都講本末內外論,但對“本”的理解不同,目的在於鞏固自身的核心地位,並在此基礎上統合三教。後世雖然儒教哲學始終佔據統治地位,但三教一體、諸宗合流的總體趨勢,也是這一時期融合論發展的必然結果。
均善論或均聖論
與本末內外論相比較,此論更強調三教和同,調融三家的傾向更為明顯。它承認三教各有其用,也各有其不足或流弊。東晉戴逵評論儒道時說,儒家“本以興賢也,即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道家“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晉書•隱逸•戴逵傳》)。宋沙門慧琳的《白黑論》雖然批評了佛教性空觀與報應說,但不否定佛教的勸善功用,主張“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宋書•蠻夷傳》)。梁武帝在《述三教師》中也說,“窮源無二聖,測則非三英”,“差別豈作意,深淺固物情”,認為三教雖有深淺之別,而向善實無不同。
殊途同歸論
殊途同歸論也包括了本末內外論和均善均聖論,但本末內外論存同而重異,以本為主,以內為主,本末內外是不平等的;均善均聖論則是存異而重同,以三教為平等;殊途同歸論則是先異而後同,或者跡異而理同,承認三教在形式、禮儀、方法上的差別,甚至對立,但認為在基本原理和終極關懷上卻是一致的。故謂之“殊途同歸論”。其說有三:第一,殊途同歸,歸在至理。第二,殊途同歸,歸在有神。第三,殊途同歸,歸在教化。第三點最為盛行。韋敻在奏獻周武帝的《三教序》中說,“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周書•韋敻傳》),都講勸善化俗,而且善惡標準一致,都是以儒家的綱常名教準則,所以三教同歸,實際上是歸於儒家的教化。這裡雖然突出的是儒教的主導地位,但是殊途同歸之說便於克服對外來文化,具體說就是佛教的拒斥心理,冷靜思考、比較三教異同,異中求同,求同存異,顯然有利於佛教的傳播和三教的匯通與融合。
三教融合論盛行,道教與儒教聯盟,依傍儒教而壯大;同時又用道家思想溝通佛、道的理論,在拒斥中吸收佛教義理,而使道教在哲學上有所昇華。其後“重玄”的道教之哲學建構,無疑得力於玄學化的佛教哲學。
佛教作為外來文化,在漢末,依附黃老方術而得以植根和流布,魏晉時期又藉助玄學豐富自己的理論而得以發展。佛教玄學化,實際上就是三教在哲理上的融合,也是中國化佛教形成的前驅先路。在這個過程中,佛教自覺地實行自身的改造,在政治上忠君,在倫理上主“孝”,在理論上主張和而不同,實行儒外佛內的分工合作,把事功留給儒教,把內聖的任務轉歸佛法,佛儒調協,使天下歸心。這也是中國宗教哲學發展的總體態勢。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